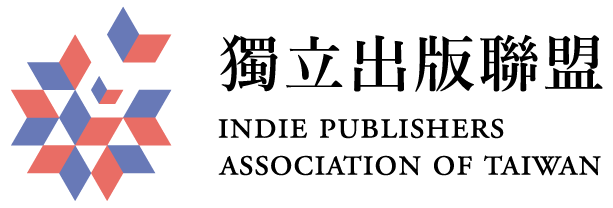文藝生活的末日世界投影──沈默《超能水滸:朱仝傳》九問
謝絕/文 林夢媧/攝影
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首獎得主沈默,在完成嘔心瀝血長篇大作《劍如時光》後,以中篇小說接連出版《超能水滸》(二〇二二年)、《超能水滸:武松傳》(二〇二三年),第三部《超能水滸:朱仝傳》(二〇二五年)直接以電子書模式上架平臺。沈默一路走來歷經多種轉變,包含創作文學小說、現代詩、舞台劇劇本、書評等,《超能水滸》發展至今,能夠清晰看見他博採各家類型小說,用心明確。究竟這個文學狂熱者想要走向何方呢?以下列出九題提問,邀請沈默暢所欲言。
一問:「什麼樣的契機,讓你開始寫作?為什麼是武俠小說類型?」
一答:「寫作最初都是為了自己。有話想說,但又極其內向封閉,對人際不感興趣,因為不想朝外噴發,理所當然地就會迴轉到內心深處,而文字是最容易使用、最貼近自我的方法。閱讀讓我認識世界,寫作讓我發現自己。
我年少時,武俠已進入衰敗期,早在一九七〇盛世後,往下跌的走向就沒有停過。但一九八〇末、一九九〇初,生活中最接近娛樂的東西,就是武俠類的小說、漫畫和影劇,很自然就會受影響。印象最深的是讀古龍《邊城浪子》、《天涯.明月.刀》,有濃郁孤獨感,加上作者本人絮語噴洩,有一種這樣寫就是武俠小說了嗎那我應該也可以的感覺,於是試著在國中時期生活週記上寫,類似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讀法蘭茲.卡夫卡《變形記》認為自己也能寫小說的感受。
從一九九九年出版第一套武俠《孤獨人》至今,說實話,我不必以武俠為本,有各種文學類型能夠寫,其實不是非武俠小說不可了。但大學時期以武俠人的身分出道,奠定我日後生活的經濟基礎。即便武俠末世臨至,武俠出版別說無利可圖,根本版稅零星,現實上來說,就連詩集都比武俠賣得更好。但最初是武俠小說出版這件事,讓我有信心成為作家,我始終感念這件事,再加上確實看見武俠還有更多可能性沒有被實踐。我堅守武俠無非是夾帶回報的意念。」
二問:「你如何堅持寫作多年?即使武俠進入末世,依然有信心持續創作?」
二答:「此前寫作練習期且不論,就從一九九九年出版《孤獨人》算起,已經二十多年。寫得久當然不等於寫得好,大家都心知肚明。寫作是努力、堅持與運氣缺一不可。但更多時候是運氣決定一切。我的第一套武俠早在大一時期就寫完,但歷經了多次投稿,直到萬象圖書才願意出版,當時他們捧紅了黃易,《覆雨翻雲》、《尋秦記》、《大唐雙龍傳》成熱銷讀物,方有意願投資新世代武俠作品。如果沒有黃易在前領軍,展露一條武俠新徑,按照當時局勢,我不太可能走上武俠職業之道。
再後來是溫世仁武俠小說大賞舉辦,我從第五屆開始參與,直到第十屆,僥倖拿了大滿貫。但更重要的是,時任明日工作室總編輯的劉叔慧,完全是我的貴人。沒有她,我無法持續在武俠小說這條路上精進至今。尤其是《天敵》、《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的出版,有人誤會這兩本拿下溫武獎項,實則不然,都是劉總編沙裡淘金決意出版。她的賞識,使我在二十一世紀初有底氣、信心繼續每年寫長篇武俠,即便無人聞問,也樂此不疲。因為溫武,有幸遇上陳雨航、宇文正、陳大為、駱以軍幾位老師的支持,甚至贈寫序文,皆是銘感五內的良好機遇。
溫武結束後,我大感茫然,雖仍舊書寫長篇武俠,但頗有見絀力竭之感,唯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藝會)數度通過我的創作計畫,包含取得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五十萬元補助的《劍如時光》,助我完成多年武俠書寫的代表之作,是武俠長路上最實在強大的後盾。出版《劍如時光》時,總編輯胡金倫、編輯黃榮慶的用心協助,朋友陳夏民、王志元、馬立群在宣傳期間大力幫忙,無疑是定心丸。其後,《超能水滸》系列亦獲國藝會以及臺北市文化局的創作補助,還有林峰毅、葉飛、劉芷妤、劉子華、李霈群、陳育萱、許赫、榮華等人的友情支援,都教我不勝感激。
近年,劉霽的一人出版社、陸穎魚的詩生活是我最佳的合作伙伴,每一次都帶來幸福感,完成了很棒的出版品。劉霽甚至願意讓夢媧和我合組的神武製作室,以一人出版社的名義,發行《超能水滸》系列電子書。
我怎麼撐下來的?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機遇。沒有遇見這些貴人和朋友,恐怕我早就登出了。努力不過是書寫者的本分,不好說嘴。我相信苦練,我不認為自己是天才,我的天分沒有那麼高,所以必須日以繼夜地鍛鍊自己。至於堅持寫作呢,並非我有信心讓武俠盛世重返,而是單純覺得武俠還有絕大可能性未曾被看見與書寫。另外,能夠堅持的關鍵點,除了自己的意志外,要感謝的還是夢媧辛勤上班,這十幾年來她的付出,讓我可以奮力深化寫作的技藝。」
三問:「《超能水滸:朱仝傳》是接續《超能水滸》宇宙觀而來的作品。你已經在不少地方談過《超能水滸》是武俠鼻祖小說《水滸傳》的性轉版本,並且結合日本漫畫家荒木飛呂彥《JoJo的奇妙冒險》替身能力,而且《超能水滸》三部都有不少書籍的引用,比如《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黑塔七部曲》等,更不用說賽博龐克、喪屍、超能力、末日等多類型元素的加入,雖說互文性本就是文學領域司空見慣的,但你不擔心有拾人牙慧乃至於抄襲的問題?」
三答:「文學裡沒有抄襲,尤其是武俠。文學是一個龐大無匹的沿用與引述系統。每個人都試著在文學宇宙裡發明自己的星光,找到自己專有的星空。誰比誰更搶先呢?這不僅牽涉到先後順序,還有鑑賞力與及閱讀量、範圍。有評論說安伯托.艾可《玫瑰的名字》受到波赫士所寫無限圖書館的影響,艾可不這樣想,他條理分明地分析自己跟波赫士都同樣是受到此前各種藝文的影響,而導致有相近概念的產生。喬賽.薩拉馬戈直截說拉美魔幻寫實根本不是新的文學類型,它本來就存在於歐陸神話、小說系統。別的不說,法蘭茲.卡夫卡的《變形記》、〈鐵桶騎士〉就超級魔幻寫實。所有文學後來者都必然走在前行者已經走過的長路上,試著踩出自己的小徑。
當然了進入現代社會,智慧財產權有確保創作者權利的美意,在這個年代,抄襲不是小事,任何相似性都可以被冠上抄襲之名。但對我來說,智財權已經變成是一種過度保護主義。抄襲這個概念比抄襲行為本身更濫用。抄襲屬於法律問題,不是文學問題。法律我很少接觸,我思考的都是文學。但為避免麻煩與爭議,我竭盡全力變換成自己的脈絡,並明言啟發我的各種原點,不會假裝那是無中生有,或說是我獨有的發明。
我沒有影響的焦慮,我本來就是文學系統的一員,我反倒很樂於展現我受到誰的影響。比如薩拉馬戈、黃碧雲與舞鶴讓我喜歡寫不分段、大量用句點的小說,夏宇讓我很少用引號,零雨開啟我大量寫詩的渴望,駱以軍讓我懂得小說過場不重要、跳過就對了,米蘭.昆德拉教懂我什麼是詩和小說史,唐諾帶我錘鍊藝文鑑賞力,伊塔羅.卡爾維諾給了我小說結構的完整訓練,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使我明白現實最魔幻,波赫士讓我對文學充滿勇氣與信念,威廉.福克納在看似破碎凌亂的敘事中完整地展露人性的複雜,塞萬提斯寫出最悲傷的荒謬、最深刻的漫遊,黃易小說實現人變成神的幻想,荒木飛呂彥完成了我心目中最好的史詩漫畫,王度廬有對人性情愛最安靜的觀照,卡夫卡讓我看到體制無意義的瘋狂,薩爾曼.魯西迪將神話、歷史與現實絞碎成體,艾蜜莉.狄金生是居住在詩的可能,司馬翎、金庸將思想變換為武功,……我可以繼續沒完沒了地說下去,但先這樣就好。」
四問:「《超能水滸:武松傳》於二〇二五年八月推出電子書修訂版,緊接著《超能水滸:朱仝傳》電子書於十月上架。《超能水滸:武松傳》書中新後記明言此一系列都將轉為電子書發行,無實體書出版。這個轉變是為何而來?」
四答:「很現實性的來說,就是市場低迷,書不容易賣。更重要的可能還是,之前實體書的出版,都讓我覺得疲憊。因為出版社花費了成本、印製的紙張全都是植物性命,所以需要用力宣傳。但對有社交障礙的我來說,每一次都很費勁挫折。
其次,我雖然熱愛實體書,但現在非常習慣用手機、電子閱讀器,時時刻刻都可讀,超級適合我這種嗜書人。這幾年間我逐步賣出手邊的實體書,轉換成電子書,例如《追憶逝水年華》、《尤利西斯》、《白鯨記》大部頭經典小說,攜帶不便,又很占空間,改買電子書後,更容易閱讀。而且電子書能夠調整字體大小,對老花眼的我,十分友善。
此外,電子書出版更自由,沒有成本壓力,且更能夠貼近自己的想法呈現,藉由各種AI工具的使用,可以順暢地製作。基本上,就是夢媧跟我一起討論與編輯,再和劉霽合作上架電子書平臺,完全不用跟其他人有接觸,無比幸福。」
五問:「《超能水滸:朱仝傳》小說一邊描繪新型瘟疫『碎疫』的恐怖,另一邊又詳述如朱仝這類自小身體有殘缺的孩子們在病院裡,遭受星魔人體實驗的暴虐景象。兩者加起來是強烈的末世感。你是從何想出這樣的結合?」
五答:「《超能水滸》是在疫情時期開筆寫的小說。最初是《劍如時光》消耗過鉅,我無力於書寫大長篇,但又心心念念想要寫武俠,百般掙扎之際,適巧Covid-19來了,整個人類世界完全急煞車。一種絕無僅有的新型末日,就在眼前發生。封城鎖國成為常態。但奇怪的是,這樣的靜止,對我來說卻是休憩的良機,因為各類接案工作全面中止。而且夢媧居家工作,學校停課女兒也在家,反倒是甜美的生活。
《超能水滸》原本就是末日小說,二十一世紀新《水滸傳》,或者說《水滸傳》末日版。眾所皆知,《水滸傳》的第一回即是「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瘟疫與妖魔是關鍵字。當然這些妖魔後來全都人類化,變成世間反賊,但最後又被體制收安。真要說起來,《水滸傳》其實也是末世小說,無處可出之人必須奮力找出求生之路,上梁山不外乎一群邊緣者建構自己的桃花源。
《超能水滸:朱仝傳》一方面書寫瘟疫事件,另一方面也試圖體現出妖魔的雙重性。同一者對超臺北人來說是妖魔,住在無電的孤島寶藏巖裡,用的也是非科技的超能力,簡直妖術。但十四星魔的作為,卻更像是妖魔的行為,各種殘虐統御五花八門千奇百怪。這部小說既是《水滸傳》主題的當代復還,同時也是我親歷的真實所感,包含大疫之世,還有人的各種妖魔化舉措。
一如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名句:『……我自己身為一個人,究竟是比百頭巨人更複雜更狂暴的一種怪物?還是更溫柔更單純的生物?』我想用跨類型小說的形式,說出『人即是人的末日,但人也可能是人的救贖』的複雜故事。」
六問:「我們都知道你是一個不怕暴雷的人,甚至覺得如果暴雷以後仍然看得興高采烈才是好的作品。但避免暴雷,在這裡還請不要細講故事內容,單就《超能水滸:朱仝傳》關於進化的精彩鋪陳與轉化談一談。」
六答:「人類和文明都是一邊進化又一邊退化的。前陣子看到一個影片,大意是說人類聰明到可以發明AI,但又笨到必須倚賴AI,更荒唐的是人類還不知道這樣究竟對不對。很可笑,但也很悲傷。
這讓我想起森博嗣在《四季》系列《冬》裡寫:『人工智慧的終點很明確,最後會成為人類,和我們沒有差別。機械會成為人類,僅此而已。但是,人類不會因此獲得未曾有過的全新伙伴。創造出來的東西只是與人類相同,不會超越人類。計算速度快、學習力強、劣化較少、錯誤也少,但它們的能力範圍,人類早已透過使用機械來達到了,創意思考的能力也相同。換言之,沒有任何特別。如果說我們在人工智慧的研究過程中有所獲得,那便是凝視我們自己,也等同於照鏡子吧。你不想要照鏡子嗎?有人類不照鏡子嗎?我們是為了什麼照鏡子的呢?想看什麼?有意義嗎?這就是這領域研究的終點。』
進化究竟是什麼呢?我這幾年對進步、進化這件事,充滿疑慮。主要是整個世界對成功學的著魔與瘋狂,使得進步跟所有東西都綁在一起,成為無敵的價值。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從歷史來看,很多時候進步演變往往帶來更大的災難。這種例子尤其是現代工業、科技以後更明顯。原本人類的進化是為了解決生存困境,但結果反而造成新的生存難題。
以文學來說,有一本要比一本更好的奇怪迷思,就如同江郎才盡、瓶頸與靈感等,是大多數人對創作者的普遍印象。我不太認同創作者全然依賴降靈的說法,那是對創作者每天錘鍊自身技藝的否定與羞辱。可是,苦練以外,還要加上各種機遇去成就。NBA球星史蒂芬.柯瑞最可怕的武器不是三分球,而是滿場飛的體力,現在三十七歲的他還能這樣跑多久?創作者的鑑賞力、品味可能會愈來愈好,但我不太相信下一本會更好的說法,因為那涉及到寫作的狀態、體力與能量。
梁朝偉今年受訪時講過,他最好的作品是《花樣年華》,那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電影了,從另一個角度來想,二〇〇年以來,是不是梁朝偉再也沒有進步、完成更優秀的作品?先不要管每個人都自身作品評斷,往往不等於他者、世人的評價。我認為,一個優秀的藝文工作者,至少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極限在哪裡,當然不是就此停頓,而是一邊持續前進,一邊清晰理解究竟完成多少足夠好、精緻的作品。
創作的定義是朝未知、不確定性出發,那不就意味作者可以持續挖掘思考的深度,但不可能完全控制。所以,米蘭.昆德拉說如果一個作者覺得他比自己的作品更聰明,應該趕快轉行。所以,波赫士才會說書能超越其作者的意圖,作者的意圖往往是凡人淺見,可能有錯誤,而書裡應包含更多意義。我真心覺得,好的作品是比作者更大的東西,作者有一部分靈魂都寄居其中,那是換取的成果,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更好。以前我會覺得自己最好的小說是還未完成、正在寫的這一本。現在呢?我很清楚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劍如時光》,那已經是二〇一九年出版的了。
所以,我進化了嗎?還是退化呢?相比於二十多年前的我,我當然是進步了,否則怎麼能寫出《劍如時光》?但同樣的,我也逐日退化,再也沒有那種日寫六到八小時的瘋魔能力。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退是順流而下,知悉自己的退,難道不是一種進化?到我現在的年紀,已明白過來,不可能有純然的進化,也不會有純然的退化。人真的是活在又前進又後退的縫隙之中。」
七問:「《超能水滸》系列中出現了很多角色,尤其每一部都是以一個小隊為單位進行敘事,雖然確實有個中心人物,如林冲、武松和這一次的朱仝。但其他角色也各有特色,會互相串連,出現在其他同一者小隊的故事裡。先前你好像講過最喜歡蕭讓,因為她的地文筆能夠移除、增加詞語的概念。《超能水滸:朱仝傳》裡,你有特別偏愛哪一個人物嗎?」
七答:「蕭讓也有出現在這本,我想她對我的重要性,可能近似荒木飛呂彥畫的岸邊露伴。而單就《超能水滸:朱仝傳》來說,阮小七很有意思,尤其是寫她使用十二張功能各異的天敗符,充滿異化精神的超能力,我自己滿喜歡。
朱仝不用說,她是整部小說的樞紐,與其說是偏愛,不如講瘦骨嶙峋、兔唇的她如何在我心中具體成形,一點一滴花幾個月的時間長出複雜的生存樣態,明明擁有強大異能,內在卻自信不足,充滿猶豫、遲疑。她的絕鋒天滿針可以縫合世間萬物,我總有她最想縫合的人應該就是她自己吧的心情,可惜兔唇與年少時人體實驗的創傷,無法遠離。但縫合的精神,本來就不在於剃除,而是將破裂重新補完。朱仝一邊覺得自身渺小失敗,另一邊又在各種關卡突破極限、展現自我能力,一如所有世間人。
認真說起來,《超能水滸:朱仝傳》我最有感的是廉貞星魔這個角色。讀者可能會預設他是反派大魔王,但我在書寫時,是隱約把自己某一些男性主義的部分投影進去,尤其是對自身進化的執迷感,也是放入了我對小說創作的瘋魔追索,一如古龍寫《浣花洗劍錄》為練武道六親不認的東瀛劍客白衣人、《三少爺的劍》心念於劍道絕頂乃創出毀天滅地奪命十五劍的燕十三。同樣的癡迷,同樣的禁絕情感。
但如果進化的終點是人性廢退,是再無生機曼妙可言,那麼進化又怎麼會是好的、值得追尋的呢?我更喜歡後來黃易《覆雨翻雲》透過唯能極輿情故能極於劍的浪翻雲,對劍道追逐的重新塑造。
技藝若是削除人性而得,我以為是入魔,而非求道。最講師匠、職人精神,但奇怪的也最著迷天才的日本夢,在規格化技藝傳承的同時,從來無意切割人情義理。近來熱播的日劇《浪漫匿名者》,乍看是兩名患有精神疾病之人的愛情故事,實際上裡面偷渡放入了滿滿的職人意念,如家傳釀酒職人那一段,一方面維護母親傳下的技藝,另一方面暗自做出配方調整,在前人嚴謹的規格裡,試圖塞入自己的心思。技藝的流傳,從來不是一人之事,是一群人花費幾十幾百年、甚至千年才能留下來的絕妙事物。
我寫廉貞星魔並不只是嘲弄諷刺男性而已,還帶有憐憫──曾經我也攜帶著那樣的認知活過來,只是現在更新了體內的軟體。我相信,男性主義者在社會提供的主要系統裡,還是能夠找到改變的可能,至少我就是如此走過來的。」
八問:「你不只一次提過,文藝生活是寫《超能水滸》系列的主要精神。但在這樣一個高速移動的時代,文學難道不可疑、又笨拙又緩慢嗎?文學真的能夠應對複雜萬變的局勢嗎?文學又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呢?」
八答:「文學是很慢的東西。因為慢,所以看起來八風不動,但其實內在是持續擾動變移的。我總覺得,文學可以改變世界。我就是深受文學滋養與改變的人。它的力量牽涉到技藝、意志與信念,本來就快不了,也不必快。
在速度與激情至上的年代,文學被掃除在現實的最邊緣,可能也不用意外。但無用與有用是相對性的。文學之用在於靈魂深處的豐美。文學的無終極解答是最教我動情的部分。我喜歡沒有答案的世界。或者換個說法,文學的答案在於文學的行進過程。繼續前進,扛著文學人種此前累積的豐厚心靈史,不武斷殺死任何一種具備生機的詮釋、體驗與思索。
唐諾說:『你得用孤寂來換取自己的乾淨、清醒和力量。』寫作是孤寂的一件事,但它同時不可思議是一種很美的相遇,或者更應該說像是同行,如零雨寫的:『我知道它的艱難了。我知道它孤獨的原因了。/它要你用時間和它交換。它輕易不和你論交,除非你真心相待。而且不是口角春風,虛與委蛇,而是要你付出青春。/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一輩子。/我喜愛的東西,都和一生有關。都是文火煉金。/我喜歡這樣的閱讀。』
文學的孤寂不是孤寂,至少在個體的孤寂裡,有一種總和性的孤寂。孤寂與孤寂相接,直通宇宙。高貴優美的事物,本來就很值得守護。當然,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夠認識、接受這樣高貴優美的東西。但有時候,過度強調高貴優美,反而阻礙了人對接近文學的慾望。文學是多面向的,可以孤高,也能通行於市井日常。我們需要更多元的與文學相遇的方法,無須獨沽一味。
重要的是,文學讓我認識自身情感、經驗與思維的侷限。無知是不承認自己不知道,而願意承認自己不知道,是一種知,也是寫作的奧義,一次又一次誠實地看見自己的無知。正如維斯瓦娃.辛波絲卡在諾貝爾文學獎致詞裡提到真正的詩人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才能前往我知道,同時又從不忘懷我不知道的基本前提。
就連森博嗣寫的那個天才人種真賀田四季也會這麼說:『有啊,正因為有不清楚的事情,人類才能變得溫柔。』是的,溫柔就在連綿不斷地認識己之無知(也旁及眾人之無知)中,火一般的升起來了。
這幾年間,我更常感覺到寫作最需要的是誠實,不是對他人誠實──對他人誠實這件事很容易淪為對誠實的表演──而是對自己誠實,專注深刻地看見自己的黑暗與極限。文學是一種相遇,而這種相遇讓人得以遇見自己。遇見,意味著直擊內心複雜世界,不躲閃,往往會羞愧不安難堪,根本不可能自鳴得意。唐諾寫:『誠實,尤其是誠實的對待自己,也得是一種習慣才行,它可以開始但不能只停留於某種靈光一閃的善念。』誠實如火,火有時會燙傷自己,但必須一直燒著內在的火焰,否則就昏暗難擋了。
《超能水滸》系列裡,我將文藝生活投影到末日世界裡,這是因為就算是末日來了,只要有文學藝術之火,就足以照亮萬古長夜與千百萬種孤寂,像戈馬克.麥卡錫反覆述說『我們要把火傳下去』,像唐諾寫『格雷安.葛林說過,赫爾岑說過,賈西亞.馬奎茲說過,凱因斯說過……仔細想,薪盡火傳的這個「火」竟驚人的準確,我認為這一準確並非偶然。火不固定,火是光和熱,火可大可小,甚至會瞬間熄掉人一無所有。所以並非只是寥寥答案,答案毋甯只是信物,是可靠的再思索支點,是新的開端云云。繼承於是呈現某種緊張感,也持續對繼承者有要求,人用一生而非一刻。』,像零雨說『我的內心燃燒著對人類、對生活的火焰。』《超能水滸:朱仝傳》也攜帶著火光,試圖在行屍走肉、疫病時代裡,照出一條明亮溫柔小徑。」
九問:「《超能水滸:朱仝傳》後記你提到光明三部曲(明三部)結束,接下來《超能水滸》系列將會邁向黑暗三部曲(暗三部),讀者應該會很好奇你對整個超能水滸宇宙的設想,為什麼要分部進行?是不是請你談一下接下來的規劃。」
九答:「早年,也就是一九九九到二〇〇八年的第一期作品,《孤獨人》、《天涯》、《魔幻江湖絕異誌》、《兵武大小說》這些系列都有一個問題,就是通通沒寫完,斷尾無續。而且更荒唐的是,當時的我總是忍不住會對讀者畫大餅,言說後來的故事如何之如何。我對此一毛病深感羞恥。所以,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九年從《天敵》到《劍如時光》的第二期作品,都是單部打完收工,不寫系列作。
《超能水滸》系列歸於二〇二〇年至今的第三期,基本上有一個大系列構想,但每一部都是獨立完整的。其實,最初計畫是《超能水滸:光明三部曲》、《超能水滸:黑暗三部曲》的形式,但深怕力有未逮,所以拆解成現在面世的模樣。
我只能說已經寫完、甚至是已出版的部分,將來的事歸將來。但《超能水滸》第四部確實有很大機會能夠在明年推出。至於後面,未竟也未知。每一次寫作都是探險,但願我能夠走完這樣的旅程。」
《超能水滸:朱仝傳》各大電子書平台熱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