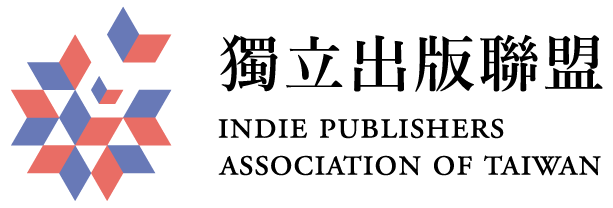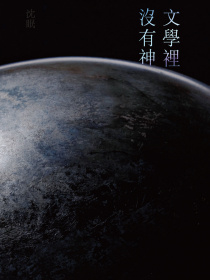夾在過去與未來・未完成的詩──羅智成×沈眠對談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林夢媧/文、攝影・詩生活/場地提供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主辦的對談活動——「夾在過去與未來・未完成的詩」,由詩人陸穎魚主持,並邀請近年以故事雲系列大展身手的詩皇羅智成,以及《文學裡沒有神》作者沈眠對談。詩齡橫跨二十年的兩代詩人,在兩個小時間以稠密的語言,進行對詩歌的多重思考與辯證,展演各自對詩形式、內容與核心的異同觀點,並旁及其他文學的諸多問題。
▉文學的遺產,龐大銀河裡的小星座
討論關於被尊為詩皇羅智成往昔作品的意義,沈眠拿起《寶寶之書》初版,「這是我在1999年買到的詩集,聯合文學版在那一年也剛好上市,不過我手頭上的是1988年由少數工作室出版、遠流出版發行的版本,現在看起來有點像是Nike裡的Jordan Brand或Under Armour的Curry Brand,私人工作室的名義,在大公司以聯動方式出版,非常稀奇。」
隨後他談起《寶寶之書》對己身的影響,「羅智成以類童話的語氣、無題的形式去組成這本詩集,總共100首詩,大多數是五、六行,最短的只有一行,最長的也不過是二十行左右,整體是偏簡短的風格,但內容卻能涵括宇宙、哲學與美學的思想,全都都放到一本詩集裡面,讓我非常驚奇,如同後來讀到費爾南多・佩索亞寫的『而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一樣。」
《寶寶之書》以數字編號進行的結構,對沈眠也大有啟發,「我本來就很偏好無題詩,比如艾蜜莉・狄金生、李商隱。而《寶寶之書》以無題詩集概念完成,是我接觸到的最早這麼做的,當然了《黑色鑲金》、《透明鳥》也都是類似的形式。後來就很容易看到無題詩集了,比如林禹瑄《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陳昌遠《工作記事》等,夏宇的《脊椎之軸》則是連編碼都拿掉了,我的《文學裡沒有神》同樣是無題詩集,但又複雜化成五種編碼系統,且將編碼與頁碼等同起來,企圖變異無題詩集,讓其樣貌更豐富。」
另外,他以沈默為筆名寫的《劍如時光》,中間部分有一鑄劍師名叫羅至乘,這是完全沒有任何打鬥的故事。最初羅至乘的乘是ㄔㄥˊ,小說裡還出現了鬼雨木的樹種,這自然是對羅智成的致敬。他不諱言地講:「一開始確實有意圖將要將羅智成的詩歌變為武俠,但後來因為放進了自己的心事,逐漸偏向為探索鍛鍊成魔的主題,羅至乘最後一個字的發音也就變為ㄕㄥˋ,隱喻著這名人物至聖一般的最初地位。」
1975年羅智成還是二十歲大學生時便已自費出版《畫冊》,其長詩代表作之一〈光之書〉完成於1976年,亦即沈眠出生的那一年。他認真說道:「年齡是無從跨越,二十年時間所累積的差距,真的是很大。對我而言,前輩們或者是以前各種作家的作品,全都是文學的遺產,我是吸收這些能量成長的後來者,是龐大文學銀河裡的小星座,像羅智成寫的『我們是真正擁有過星星的』。」
▉以水平思維模式,展開對詩歌的探索
陸穎魚表示,有一回羅智成到詩生活舉行講座時說到,詩是他的工具。陸穎魚非常震撼,因她總覺得詩的位置比詩人更高,從未有過可以操控詩的念頭,也就更好奇羅智成的心智強度與高度,何以能夠凌駕在詩之上。再加上羅智成的創作能力始終很豐沛,早已累計許多經典作品,因此非常想聽羅智成針對已成輝煌的過去,還有對詩歌未來的想像與經營,談談自己的想法。
羅智成把詩視為一種工具,每個人都可以用它來做到認為詩最適合做到的事情,這是一種態度。他強調,有些東西將之看得太重的話,反倒沒辦法有效運用,變成像是在供奉它,可是工具再偉大、再誠心膜拜,沒有好好的使用,終究是虛的。
羅智成滿臉笑意講述,剛出道時,便被譽為早慧的詩人,因為很年輕就開始發表作品。但到了現在,他都會自開玩笑,已經三次延長了青春期,應該到九十歲都還是一樣吧,而且他並不介意用年輕化的形式來表述。羅智成說:「我想,這是由於我一點都不想要放棄過去的自己,我是帶著自己的童年移動往老年。」而《寶寶之書》即是羅智成以神祕絕倫的語句、宇宙般廣大的思想,重新完成自己未完成的童年。
「因此,陸穎魚訂的題目對我來說是相當有意思的,過去與未來不是兩個端點,對我來說,時間並非線性發展,而是同時存在。」他頓了一頓又說:「詩歌也同樣不是線性思考,更像是一種水平思維模式。線性是有前後上下的區分,但平面是一種過去與未來都平等並置的狀態。越到後來,我越發現自己捨不得把過去放掉,我沒有真正放掉過那些,我一直帶著它們,企圖擴大那些過去的事物。水平思考的想法,如今占了我生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而當我這樣思考的時候,就能感覺到靈魂持續在增長。」
至於詩的進化論,羅智成如此闡述著:一個人一開始就是顛峰,似乎就意味著他後來只能走下坡了,但創作本不一定是越寫越好,大部分都是越寫越差,詩是不可能越寫越好的。他率直地說:「有人說我一出道就是顛峰,這是很大的讚美,但我難免要想那麼接下來也不太可能進步了。但這樣的想法是單向式的,我更喜歡反過來思考,去打破原來的確認、既知。」
羅智成認為,跳脫固定制式的線性思維,才能持續保持創作的動能,他表示:「創作本就沒有真正的美的典範,每個人不同時期都有不同時期的美感。一個人就可以是一個宇宙。我們要曉得自己不是只有一種可能性,而是多樣的豐饒的可能,攤開在眼前。每個人都被迫從過去走向未來,所以對未來都有憧憬,相信未來都更好。但真正能觸動我的,都是過去。如果不用線性思考的話,而是平行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那麼我們在每個時期都得以完滿。」
緊接著,他話題一轉地談及,創作者要對抗的對象,從來不會是外面的對象,要去對抗某個人、某件事或某種形式,是相對來說太容易的事了。於他而言,最大的假想敵應該是自身。羅智成說:「尤其是對過去想法和慣性的否定,更該是創作最重要的狀態。每次對抗既定已知的自己,我就會感覺到自己又變得更大了一點,這不就是最完美的對抗嗎?而對抗自己就像齊天大聖孫悟空,一拔毛就吹出了更多的孫猴子,變化無窮。但沒有說哪一個才是真的,因為每一個都是你。」

▉在平庸的事物裡,找到自己的詩
在談故事雲系列之前,沈眠先說了一段話:「波赫士老年時在小說裡寫著,一個詩人如果是詩人就始終是詩人,他會感覺到詩意始終在衝擊著自己。而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是,詩歌是少年的藝術?還是中年的藝術?抑或者是老年的藝術?」
羅智成二十歲之齡便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畫冊》,隨後幾年有《光之書》、《傾斜之書》接連問世,三十四歲推出《寶寶之書》、《擲地無聲書》,四十四歲則是《黑色鑲金》,且陸續將過去詩集重新修訂,也就是現今市面可見的聯合文學版,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羅智成六十歲以後仍持續寫出故事雲系列作品,至今有《迷宮書店》、《問津:時間的支流》、《荒涼糖果店》等。
沈眠分析:「從敘事詩到故事雲,這裡面的變化,主要是用詩歌說故事。敘事詩還謹守在詩歌有固定形式、語法的路,但故事雲壓根甩開了詩歌既定的認識,大量用了小說、劇本、散文等其他文類的元素。羅智成在粉碎過去的自己,但又把那些碎片重組成現在的自己。這些作品也就更像是巨大的思想,且在示範著詩歌的疆界永遠可以往外突破。畢竟,詩如果只限定於某種想像和定義,那就不是詩了。」
米蘭・昆德拉的《生活在他方》是一部極其狠辣地批判抒情詩人的小說傑作,但對沈眠來說,反倒是他更清楚地意識到什麼是詩,或還有什麼可能是詩的啟蒙鉅著。「詩不會只出現在詩歌裡,詩會在小說、電影、漫畫裡,詩也會在日常裡忽然顯影,比如我女兒的一句童言童語,又或者是我太太的睡顏裡。詩意是翻轉你所在的位置、此前的認識,讓你下墜或上升,世界在那一刻裡被徹底翻轉了。而詩歌不過是一種人類打造出來能夠最直截通向詩的形式。詩歌不代表必然就是詩。有些詩歌完全抵達不了詩,還不如一部具備詩意的動畫電影。」沈眠直指核心地論說著。
旋即,他講到艾德華・薩依德的《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裡面以貝多芬的音樂作品為例,到了老年,他並沒有變得合群,風格不是平緩的寧靜的,反而更破碎、尖銳。另外,書中也提到現代主義,如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往回探溯,結合了歐洲神話、傳說與悲劇,亦即藉由返回過去的機制成就了現代主義。
「所謂的晚期風格不是老年寫作,不是重複以前既定風格的延續,而比較是一種全新的觀念,勇於抵抗現代的潮流,但養分拉回到更久遠以前時代的文藝風貌。那並非是選擇和年輕化的世界或年輕人站在一起,而是重新錘鍊成新生,像是從晚年之中重新打造出童年,一種敢於和世界作對的意志。米蘭・昆德拉的《無謂的盛宴》也是這樣,終其一生跟人類非理性打戰的他,持續深化,且十分尖銳地指出現代人類那種狂歡、節慶的無意義。」
另外,沈眠很喜歡的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法蘭索瓦・歐容,早期他們的電影都是如詩如畫,每一格畫面都美得不像話,即便處理暴力動作也帶著詩意的觀照,但近期作品就不再講求鏡頭的雕琢,反而是更專注於說出足夠完整的故事。
沈眠的眼神專注地像是抵達了另一個宇宙,「波赫士說變老了之後,就更能直接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我想,那是創作者奮力了一輩子,最後才能夠透露出來的聲音和靈魂。波赫士的很多作品,如〈環形廢墟〉等,都會提到一個觀念,時間既是朝前,也是往後的。而《沙之書》裡,波赫士也寫過年老的自己遇見年輕的自己,彼此分享近況。創作的奧義在於,把過去的自己和未來的自己都包納在此時此刻,我們終究只有現在,可以連結著過去跟未來。我想,羅智成的故事雲充滿這樣子的創作自覺,是一種少年、中年和老年同時並存的藝術。」
停頓幾秒,沈眠又馬不停蹄地提出90年代蔚為風氣的媚俗,那是來自昆德拉的概念。他的語氣鏗鏘,「以我自己來說,媚俗無非是對平庸投降。年輕時當然會非常熱切地想要拒絕平庸,想要特立獨行,成為意志清明的少數者。但現在卻不免會多想了一點,平庸真的是那麼可憎、罪惡的東西嗎?人不都是平庸的嗎?再怎麼偉大神聖的人,身上也一定帶著平庸的部分。」
在他眼中,過去文藝各種新興的主義、潮流,最後都是會過時的,無論是多麼教人驚心駭異的文學,比如超現實、後現代,當每個人都能寫得一樣時,也都已經變得平庸。他赤誠地說著:「在每一種潮流裡,都必然有著反潮流,最好的自覺是看到這些潮流是同時存在的,但專注地陳述與表達自身情感與思維。從平凡無奇的日常裡,看見驚奇,在世俗之中找到空間,容納真正想說的話。創作者不都是要在平庸的事物裡,找到自己的詩嗎?」
沈眠很偏愛的大小說薩爾曼・魯西迪有一本類童話小說《哈樂與故事之海》,其中情節是哈樂的爸爸是喜歡講故事的掰王,媽媽則喜歡跳舞,但有一天這兩個人的能力都失去了,於是哈樂因緣際會前往故事之海,要找到讓故事重新從爸爸嘴中噴湧出來、媽媽熱情跳舞的可能性。沈眠揮舞著手勢,「魯西迪在1980年代寫的《魔鬼詩篇》、《午夜之子》等,帶著絕大的幽默對準宗教、政治、歷史、藝術進擊,早已是經典。1990年的《哈樂與故事之海》看起來很輕薄,但裡面仍舊裝載了豐富的神話、文學藝術元素,我深受震撼。我也是一個想要前往故事之海撈故事回來的人,或者像是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燈光似水流〉寫的那樣,扭開水龍頭光就出來。所以,故事和光不會消失,就像驚奇感不會消失,是眼睛看不見,是心再也不願意去感受。」
沈眠復又提到Netflix影集《超感8人組》,其迷人的部分在於,不同國籍、不同地區、不同性別的八位主角,會忽然就降臨到對方的所在地,親身體驗那個絕無可能到達的現場,身體與心靈的界線全都被破除了。沈眠動容地說著:「文學追求的應該就是這樣子的共感,可以藉由作品去跟作者對話,突圍了時空限制的超連結。一旦我們深入別人故事現場,那就會變成自己的故事。波赫士說一首成功的詩最重要的是表達渴望。羅智成的故事雲裡,就具備著對詩歌、故事和世界的渴望。」

▉詩的三大功能,抒情、敘事和說理
談到敘事詩的變化和突破,羅智成自陳在很早期便已經有企圖經營了,比如《傾斜之書》的〈入冬前的雨季〉就是一首完全沒有任何標點、大塊文章的長行長句詩。「抒情、敘事和說理,是詩的三大功能。我打從一開始就不想只選擇一種,我想要的是這三種面向都能全面發展。很多人誤會詩歌只能抒情,但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而當詩人想要在詩歌裡說道理時,往往只能採取大聲疾呼的激情、要披露一顆赤子之心的態度,我是有點不以為然。」羅智成肅然而語。
為什麼詩人不能寫出優秀的說理之詩,只能像是小孩一樣的吶喊呢?羅智成直白地講:「用詩來講道理,的確是非常難的事情。但我認為,最美麗的思想就是最美麗的修辭學,能夠把自己想的事,好好寫出來本身就很漂亮。我喜歡想事情,然後以詩的形式寫出來,寫出來是不是詩,我沒有那麼在乎,因為思想本身就很珍貴啊。」這也是為何他在《光之書》輯七「語錄」有注音符號為標的同名詩〈語錄〉,裡面寫的都是羅智成的所思所想。
「我創作故事雲的時候,更想要用別的形式,來表達對中文現代詩的質疑。」羅智成開宗明義地說著:「我們對詩的想像實在太小了。詩是很大的,並不是我想要把它做大,而是詩本來就很大。早期所有的史詩形式,都是用詩進行的。韻文可以說是人類最早的文學形式,而詩就是韻文的極致,但也因此詩被迫越來越精緻化,包含必須遵守押韻與字數等等,當然就會對表述空間造成影響。」
他以五言絕句的四字五句二十字限制為例,能表達的非常有限,所以就會逼創作者要在有限的空間裡去展現能量,每一字一詞都無比重要。羅智成耳提面命地講著:「詩是高度依賴讀者的文學形式,亦即讀者必須具備同質性,了解作者放在詩裡的意象、隱喻和典故。詩的門檻很高,要引發觸動、共鳴,閱讀能力就得要拉高到一定的程度。這就很像笑話,在我看來,最接近詩的表達形式是笑話,笑話不用多加解釋,懂的人就懂,大家都心照不宣。」
羅智成自然會在詩歌裡大量運用意象和技巧,但當他意識到自己想要對更多人表達的時候,就勢必得放棄某些典故、意象。「當我想要用詩講故事,尤其是寫到三千行的時候,就不可能放入太多隱喻,讀者根本不可能讀下去,因為劑量不對,太濃稠了,沒有多少人有辦法容忍那麼多的意象持續噴發著幾百、幾千行。詩就像舞蹈,散文則是散步,人不可能跳舞跳整天,但可以散步慢慢走很久沒問題。」羅智成慢條斯理地分析道。
寫故事雲系列,他便有意圖地善用文字去擴大詩,不讓詩歌受限,故事雲就像是交響樂一般,展現了他對詩歌更可以是什麼的新想像。他神色淡然地說:「其實詩可以做得更多,不要只用詩的句型去決定什麼才是詩,也不需要每首詩都應該是espresso。詩的可能性何其之多,放寬詩的範疇,讓包容性變得更大。每個人的特性都不一樣,對詩的感受也自然有所不同,自然可以各自堅持自己喜歡的詩歌樣貌。以我來說,也越來越少在詩歌感到震撼,而是在如《愛X死X機器人》這樣的動畫裡,獲得更多詩的感受。核心不能看不起邊緣,唯有不斷朝外擴展,才能突破現有的疆界。」
羅智成的語調裡洋溢著信心:「沒有一個人寫詩的時候,確定自己寫的是詩,所以很多人的壓力都是要寫出自己看過、最像詩的東西,這樣一來,反而讓自己離詩越遠了。我在《光之書》最後一首詩〈芝麻開門〉劈頭就寫『……我的性格結構已愈不適合寫詩╱我要創作適合我的詩』。創作者得要有自信寫得跟別人不一樣,但仍舊很清楚那就是自己的詩。這當然很孤獨,然而多年後再回顧過去的每段時間,就會發現真正可以留下的就是那些作品,在那之中都能看到自己。」
陸穎魚則分享她剛開書店的時候,也常會有究竟什麼是詩的疑問。有她自己喜歡的詩,也會有不是那麼喜歡、甚至覺得好像不是詩的詩集,但一間書店裡什麼詩都得賣啊。陸穎魚最後為講座總結:「我記得零雨說過,太陽只有一個,每個人看太陽,都有各自的角度。我們就站在自己覺得美的地方去看就好,不用強迫別人跟自己在一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