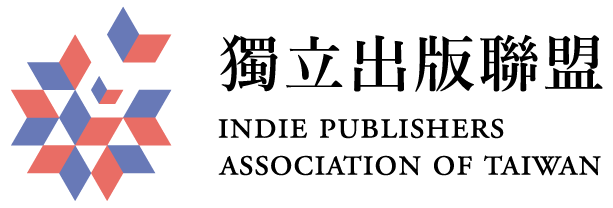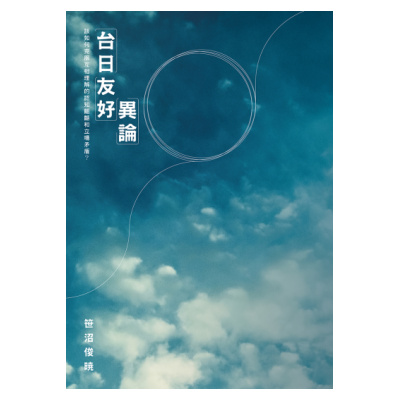
填補二戰後當代史的認知空白,體察地緣政治下的幽微情緒
相互凝視當前的政治社會實況,踏實耕耘促進多元民間交流
「台日友好」的終極理想目標——攜手對抗各種隱蔽的暴力
旅居台灣近二十載的日籍學者笹沼俊暁以中文書寫,面向公眾讀者,發出異於主流聲音的異邦人之言。從跨境的視角,批判反思橫跨台日間的思想矛盾與認知落差,以評論洞見做為增進相互理解的中介橋梁。期盼台日公民社會透過各種交流管道,一同促進彼此「學習∕回饋」迴路起作用,令雙方「贈與∕互酬」機制活絡運作。寫作本書正是此種努力的一環。
《「台日友好」異論》不是一本反對友好的書,而是一部追問「友好」真正意義的作品。作者以銳利而誠懇的視角,挑戰表面化的「友好」想像,直面歷史與權力的不對稱。本書從未否定友誼,而是提醒我們:真正的友誼不應害怕衝突,唯有透過批判與理解,才能抵達彼此真正看見的地方。
這部評論集宛如時間膠囊,封存了一位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者∕評論家,對於真實世界的動盪變化(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東京奧運、台海危機、安倍晉三遇刺、能登大地震等)的沉思與抒發。如今以嶄新架構編排而成的文集,向後疫情時代,身處「台灣有事」陰影下,憧憬「台日友好」的讀者們敞開,發出閱讀、思辨及對話的真摯邀請。
◎台灣該如何面對日本的危機
台灣人普遍認為日本是民主國家、日本的民主沒什麼好擔心。然而,「川普2.0」證明了在任何國家,民主都是易碎的。其實,近十幾年來日本的民主不斷面臨破壞危機。
◎日本國憲法與台灣
近年來國際社會激變,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正處於嚴峻的考驗時刻。甚至台灣有民眾表示,希望日本修改和平憲法,可以為保衛台灣出兵。台灣民眾真的願意日本放棄和平主義理念嗎?
◎在疫情之下反思台日當代史
現在須再度反思的,不只是疫情期間哪個國家較優秀、哪個政府較差勁,更是當時所顯現出來的社會格局及其歷史背景為何。否則,未來「另一種危機」來臨時,那樣的社會結構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讓問題爆發。
◎日常生活中的台日矛盾
橫亙在台灣和日本之間的矛盾、齟齬,不僅存在於抽象言論中,也可以從日常生活的某些傾向、行為習慣察覺出來,而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術論述不一定關注這些瑣碎事情。
◎面臨潛在浩劫的台日民眾
人類每當面對自然災害時,雖然受創、受苦,卻總能擺脫危機,重建生活。但核電帶來的災害則完全不同。輻射污染會讓一塊土地變得幾乎永遠無法居住,而且核電廠集中象徵著一國政治、社會、經濟等的矛盾。
各界推薦
「很喜歡作者『人間清醒』的姿態,不為批評而批評的清晰立場。同樣身為在台外國人的我,在閱讀的過程中獲益最多的是作者強調,我們其實是不斷透過『他者』讓自己的『學習/回饋』的迴路起到作用。看到這裡,我有一種『啊!確實是如此』的感覺。也就是這種想法,讓我們需要不斷去發聲、去碰撞、去挑戰既有概念或制度,其實都抱著為台灣社會盡一份力的心意。」
——王麗蘭(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助理教授、《田野特調》共同作者)
「《「台日友好」異論》是一部罕見而誠懇的著作。作者笹沼俊暁身為長期居台的日籍學者,選擇以中文書寫,不只是語言上的努力,更是一種理解與對話的實踐。他以冷靜而急切的筆觸,試圖穿透台日關係中那層被禮貌與懷舊包裹的「友好」幻象,直面雙方歷史、權力與認知上的不對稱。這本書並非反對友好,而是要讓友好回到現實的深處——唯有看見矛盾,才能談真正的理解。面對那些以符號化、標籤化方式簡化台日關係的論述,他以思考與真誠正面回應。這樣的書寫,是智識的勇氣,也是情感的責任;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友誼,應從誠實與反思開始。」
——陳思宇(凌宇出版總編輯)
「閱讀笹沼俊暁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戰戰兢兢,字裡行間讀得到他用力的獨立思考,與真心誠意。在這言辭浮濫各擁其主的年代,像笹沼俊暁這樣獨立、用力寫文章的無緣者,格外值得敬佩。」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台灣與日本很像一對離異的夫妻,各自再婚,經過幾十年,重逢後陷入盲目熱戀,因為彼此腦中呈現的都是青春時期的對方,再度天雷勾動地火。然而,過去幾十年各自歷經的痛苦與成長,都被眼前的粉紅泡泡所遮蔽,彼此甚至不想去深究。
居住台灣十多年的本書作者笹沼俊暁,特別直接以中文書寫,向台灣人直指當前這種親日哈日風潮,最大的癥結在於不理解日本人於二戰後,在知識界甚至普遍的國民意識上,花了數十年深刻反省發動戰爭的罪惡,由此產生的和平主義思維。相對地,日本人則較少認識到,台灣人在二戰後受國民黨威權統治數十年,在民主化歷程中形成了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又在面對中國武力壓迫下產生出國家建構意識。
本人曾實際接觸過日本的社運界,無論是勞動、婦女或環保團體成員,大都有強烈的反戰意識,認為武裝日本就是挑釁中國,令我心中充滿問號。不過,想想回到日本曾是戰爭發動者的脈絡,有批判意識的日本人當然會深刻檢討,我也就釋懷了。
作者苦口婆心地書寫,台日彼此在戰後形成的深層意識中有其內在衝突性,如果雙方沒有更深刻地相互理解,那將無法長長久久、真心相待地台日友好下去,此乃苦口良藥也。」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在台日人』笹沼先生,以其獨特洞察力與批判意識,剖析安倍政治遺緒和新宗教問題的負遺產,反思學歷崇拜與反智社會的困境,又以文學研究專業,從文學作品切入現下政經議題的另類視角,勇於掀開『台日友好』的潘朵拉盒子!身為『在日台人』的我,閱讀過程中不斷直面自己的『友好幻象』。
在時下社會氛圍中,完美呈現台日友好面就能自帶流量之際,笹沼先生仍維持批判意識的清醒,令人敬佩。台日友好『異論』提醒著,友好不是『無視』問題,而在於『直視』矛盾、面對差異。本書值得所有參與台日交流的文化工作者與公民團體、關心台日關係的政治工作者,以及往來台日兩地的讀者們細讀,一同在異論中對話前行。」
——許秀雲(台日文化交流統籌暨口譯)
「從《流轉的亞洲細語》,到『獨立評論@天下』專欄『和僑鄙言』集結而成的新書《「台日友好」異論》,是一本由日語母語者寫給台灣人的中文『情書』。
笹沼老師三十二歲來到台灣後才開始學中文,他以中文書寫並非工作需要,也不是為了討好台灣人,而是想實踐他對『逆・少數文學』的理想——屬於強勢語言社會的作家,投入相對弱勢的語言社會及其讀者空間,並在當中開展創作。這樣的社會實踐,有極高的理想性。
身為旅台異邦人,他很清楚當代台日之間有著思想分歧、扭曲、不平等的各種矛盾,深刻影響到雙方的相互理解,他帶著問題意識,企圖為讀者分析這些台日間的誤解。
笹沼俊暁大膽無畏地提出與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意見,對『台日友好』或日本政治人物不吝批判,這種逆風書寫也許讓人感到違和,覺得『這人不懂我們台灣人的情緒』,但他以中文發聲的理由,並非為了奉承台灣主流族群的國族情緒,而是對台灣的一份『回禮』,期待大家一起打開這份禮物。」
——廖雲章(「獨立評論@天下」頻道總監)
作者簡介
笹沼俊暁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教授。197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現居台中。著有《「国文学」の思想:その繁栄と終焉》、《リービ英雄:「鄙」の言葉としての日本語》、《「国文学」の戦後空間:大東亜共栄圏から冷戦へ》、《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目錄
推薦序 「無緣者」的獨立評論/張正
序 被隱蔽在台日友好矛盾中的旅台日人
第一部 台灣該如何面對日本的危機?
日本的「戰後民主主義」與台灣
日本的戰後民主主義,對當代台灣民主有什麼意義?
安倍身後留下的,是一個如同打開潘朵拉盒子的日本
——從日本當代政治思考台日關係(上)
《麵包與馬戲團》政治娛樂小說反映出日本社會的歪曲
——從日本當代政治思考台日關係(下)
近代日本的「敗者」與上野公園
——讀柳美里《JR上野站公園口》
對抗被隱蔽的暴力之「台日友好」
第二部 日本國憲法與台灣
烏克蘭戰爭下,在台灣重新思考日本國憲法
日本護憲派的困惑和混亂
——烏克蘭戰爭下,在台灣重新思考日本國憲法(二)
論《這裡是羅德斯:東亞國際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從「小國主義」角度反思台日關係
由於都經歷過苦難歷史,台灣人和沖繩人必定能互相理解
——在日台灣人作家的苦惱和他所寫的沖繩
第三部 在疫情之下反思台日當代史
日本防疫政策的失敗與大日本帝國的亡靈
從日本二戰後的社會發展,看台灣新冠病毒「總體戰」
染疫太多就不要檢測吧!
——蒙住眼睛不願面對疫情的日本人
在日本,「右翼」到底是何種存在?
第四部 日常生活中的台日矛盾
我為何書寫中文?
——一個日語母語者在台灣的困惑和煩惱
我為何不能說日語?
——擁有白人面孔的日語作家,在日本的困惑和煩惱
日本人都守時有禮、台灣人都熱情不拘小節?
——台灣眼中的「日本刻板印象」與自我形象
頂大菁英的空殼
——從日本學歷主義思考台日社會
讀書無用與民粹
——從反智主義思考台日社會
第五部 面臨潛在浩劫的台日民眾
日本的噩夢
——「南海海槽大地震」與富士山噴發,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在地震大國蓋核電廠
——為何日本不應該重啟核電?
在地震與核災面前,日本社會的隱憂
戰後日本產業社會的瓶頸和核電(一)
——日本如何引進且推行核能?
戰後日本產業社會的瓶頸和核電(二)
——在日本反核運動有何種意義?
結語 未來台灣和日本該往何種方向走?
後記
序言
推薦序 「無緣者」的獨立評論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我的日本經驗,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算。公元一九七九年,中華民國六十八年,老三台聯合製作的《大時代的故事》在元旦開播。(註1)第一集,主持人端坐鏡頭前,配合史料,悲憤又激昂地從滿清腐敗、孫中山創辦興中會談起,第二集,談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的甲午戰爭,節目持續播出兩年,以對日抗戰勝利作結。這段中華民國史,日本是貫穿頭尾的反派主角。
討厭日本
做為一位「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小學三年級的我,當然要每週守在電視機前,乖乖地、認真地、心痛地看《大時代的故事》。雖然偶爾也會覺得某些情節怪怪的,例如,為什麼盧溝橋的另一頭有日本部隊?「民族救星」蔣公aka蔣中正為什麼忍了這麼久,才突然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喊抗日?而日本這麼壞,「我們」這麼恨日本,為什麼抗戰勝利之後卻又「以德報怨」?是因為民族救星早年留學日本嗎?
小學生的我沒有能力理解上述細節,也許心中留存了對日本的反感。但是反感歸反感,生活裡仍是滿滿的日本。卡通、漫畫、日劇、食物(尤其生魚片)、家電汽機車(例如「來自日本、非常稀少的壓縮機」)、甚至「和製漢字」(わせいかんじ),都是日本產物。曾經讓年輕的我廢寢忘食的村上春樹,也是日本作家。差點忘了,大學畢業等待當兵的那個夏天,我還去學了兩個月的日文,以為日文裡很多漢字,應該很好學。結果當然是沒學會,我把日文想得太簡單了。
出身於討厭「小日本」的外省家族、而且全盤接受義務教育反日史觀的我,在與本省籍妻子交往、結婚之後,遇到了成長於日本時代、到離世之前都摯愛日本的妻子的阿公阿嬤。妻子說,他們家族的小孩只要去日本玩,阿公阿嬤都笑逐顏開大力稱讚,甚至出錢贊助。就如本書作者笹沼俊暁所說:「台灣民眾長年來懷有的『日本=該學習的先進國家』觀念。」而我的小姨子也是日本文化愛好者,至今仍孜孜不倦地學日文、看日劇、追逐日本偶像。
啊,同為台灣人,對日本的態度真的很不一樣呢。
閱讀日本
我認真開始試著了解日本,是在研究東南亞議題之後。因為我「發現」,相較於數百年來蠶食鯨吞東南亞的歐美列強,日本竟是唯一曾經全面統領過東南亞的強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除了跨越換日線偷襲珍珠港,也秋風掃落葉般攻占美國統治的關島和菲律賓,以及英國所屬的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而後入侵泰國、緬甸、印尼,幾乎「統一」了東南亞。
日本怎麼這麼厲害?我囫圇吞棗地讀書找答案。在《公司與幕府》,讀到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幕府前卑躬屈膝,以及日本在東亞秩序的角色;在厚厚的《「日本人」的界限》,讀到日本帝國擴張之後,如何傷腦筋安排日趨複雜的組成族群;在《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讀到日本殖民者強制台灣原住民遷移部落的背後,有著理蕃、拓殖、林業、教化等等彼此扞格的動機與各政府部門的角力,倒未必是為了破解反抗勢力(但剛好有這個效果);在超級厚的《帝國落日》上下冊,讀了一遍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由盛而衰的始末;也讀了司馬遼太郎懷著對台灣深深的感情所寫、備受讚譽的《台灣紀行》。
大約就在此時,熟悉日韓的朋友陳思宇推薦我讀笹沼俊暁的《流轉的亞洲細語》。
笹沼俊暁苦學中文,有意識地以中文解析日本文學作品中的台灣、中國形象,檢討日本主流社會對於異族、異文化的漠視與偏見,他也以長年生活在台灣的親身見聞,戳破台灣人對於日本的刻板印象。而我剛剛讀完的《台灣紀行》,更被笹沼俊暁用力撻伐。他認為司馬遼太郎只與通曉日文、喜歡日本的台灣人交談,便以不完整的經驗建立了「親日台灣論述」,偏偏,誰不喜歡聽好話?於是主流日本社會得意地「接受」了台灣的喜歡,而忘了日本曾經以暴力殖民台灣。
笹沼俊暁的《流轉的亞洲細語》,毫不留情地反思反省到骨子裡!謝謝陳思宇的介紹。讚嘆之餘,我推薦笹沼俊暁給主持評論網站「獨立評論@天下」的妻子廖雲章,看能不能邀請他開專欄。
和僑鄙言
於是,笹沼俊暁開始在「獨立評論@天下」開闢專欄「和僑鄙言」,以中文面向普遍喜愛日本的台灣社會,一篇接著一篇,像刻鋼版一般用力地寫下誰也不討好的評論。這本書,則將笹沼俊暁的專欄文章分類集結,方便讀者完整了解笹沼俊暁的用心良苦。
做為一位遠離原鄉、長住台灣、但與在台的日籍同胞格格不入的日籍人士(他對於日本人在台灣但不學中文頗有微詞),笹沼俊暁自我定位為「無緣者」。(註2)但是呀,這位多方無緣的無緣者,卻又對現實世界的現象多麼急切!他檢討日本右翼政府的失能,烏鴉似地為日本極可能遇到的大災難發出警語,更尖銳挑戰「台日友好」的內涵。笹沼俊暁提醒台灣,「先搞清楚日本政界的意識形態」,因為目前日本政界與台灣友好的,「偏向於那些鷹派,甚至包括與新納粹團體有關係的人士」,恐怕造成台灣的危險。
笹沼俊暁痛恨台日之間膚淺的好來好去,「台灣人的日本形象中,後藤新平、八田與一之後,接著就是哆啦A夢、魯夫」,忽略了二戰之後日本社會內部的激烈對抗。他當然也數落大部分日本人心中貧乏的台灣形象,「幾乎只由珍奶、小籠包、台北一○一以及日式房屋、老人家所講的日語等日據時代留下的痕跡構成,很少想像中間曾有過什麼樣的二戰後歷史。」
閱讀笹沼俊暁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戰戰兢兢,字裡行間讀得到他用力的獨立思考,與真心誠意。在這言辭浮濫各擁其主的年代,像笹沼俊暁這樣獨立、用力寫文章的無緣者,格外值得敬佩。
【註1】選在一九七九年大費周章地製播宣揚中華民國史觀的《大時代的故事》,並將這年訂為「自強年」,當然是因為這一年,美「匪」建交,中華民國被拋棄,民情沸騰。至於日本,哼,更早之前就和我們斷交了。
【註2】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無緣社會(日語:無縁社会)是二○一○年日本放送協會《NHK特集》播出的探討人際關係疏遠的專題,而後發展成一個新創詞,意思為:「在高度成長的過程中,許多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被打破,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再有任何關係及血緣。」所謂「無緣」,是指一個人失去所有緣分連繫,總括三大緣:社緣、血緣、地緣。
序 被隱蔽在台日友好矛盾中的旅台日人
本書中的文章大多來自二〇二一年七月至二〇二四年二月在「獨立評論@天下」上發表的連載專欄「和僑鄙言」。自二〇二一年迄今,台灣、中國、日本以及世界各國發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事件,如新冠病毒蔓延、烏克蘭戰爭爆發、東京奧運、台海危機論述盛行、安倍晉三遭刺殺、日本能登大地震等等。在本書中,我藉由這些時事問題談論在約十九年的台灣生活中我時常思考的事情。
然而,我畢竟是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者,而非政治學、社會學的專家。書中有些內容含有為提供讀者、我自身思考材料的「假說」,不一定基於人文科學專門領域的實證研究,而有些部分則是介紹在日本社會或學術界中早已流通的論述,同時向台灣讀者們表達我自身的想法。因此,本書不能說是正統的學術專書,而是為一般讀者書寫的社會文化評論集。不過,若本書有稍微獨創的部分,那就是從一個旅台日籍人士的「跨境」處境之角度,批判地反思與評論橫跨台日間的思想矛盾,並且為台灣一般公眾直接以中文書寫。
先前我之所以取「和僑鄙言」這個專欄名稱,是因為身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我希望從「異邦人」角度發出與台灣主流思想不同的聲音。也就是說,我本來意圖讓「鄙」一字代表著思想上的「邊陲」,但沒想到竟然有幾位朋友跟我說:「你怎麼那麼謙虛。」其實我絲毫沒有「客氣」念頭,但似乎由於我的中文語感不足,而沒想到竟然令人聯想到「日本民族性」刻板印象。由於如此,本書重新取了書名,以免造成誤會。
台灣和日本之間的思想矛盾、齟齬
約五年前,我出版了《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游擊文化,二〇二〇)一書,那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以文藝評論形式談論以台日為主軸的東亞思想問題。書寫那本書時,我盡量考慮一般讀者,但畢竟是文藝評論,且我只不過是一個無名作者,能獲得的讀者數量、範圍難免受限,但後來幸好能得到在「獨立評論@天下」上發表文章且向更加廣泛的讀者層直接發言的機會。事實上,剛開始連載時,起初我沒有明確的核心理念,而只是籠統打算透過各種社會事件、文化現象、歷史背景等隨心隨意寫下我自己的想法而已。但現在回頭來看,發現那些文章的背後一貫有著一個問題意識――當代台日間有著思想分歧、扭曲、不平等等各種矛盾。
我本來在日本出生長大,專攻日本近現代文學,三十二歲時遷來台灣。在那之前,我幾乎只在日本國內的社會思想脈絡中思考各種問題,沒認真意識過日本與其他亞洲地區之間存在著,社會意識、思想脈絡、思維方式等的矛盾、分歧。但在台灣的長年生活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台日間的思想齟齬其實相當嚴重,並且深刻影響到雙方的互相認識。
關於台日間的矛盾,我從前在推特(X)上曾以日語寫下如下內容,獲得不少贊同。
①許多日本右派、保守派欣賞台灣的「親日」一面,卻不願意思考台灣政治社會的先進一面。
②不少日本左派、自由派過於稱讚台灣的先進自由一面,卻忽略其黑暗面向。
③部分日本左派、自由主義者過於小看在國際社會中台灣所處於的危機。
④不少台灣人士對日本右派的「親台」示好,但忽視其反民主主義、反自由主義一面及其危險性。
⑤不少台方人士忽略日本戰後民主主義、和平主義,也過於輕忽許多日方人士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的歷史。
不用說,不僅對日關係,台灣與其他國家之間也有彼此認識上的問題。但在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特殊脈絡下,台日間形成的思想矛盾特別嚴重,就如難以解開的亂絲一般。令人頭痛的是,基於這種矛盾的互相認識,與許多人士自身的身分認同、政治立場息息相關,他們往往沒意識到那是「問題」。然而我認為,若要推行「台日友好」,首先該做的就是反思自己而認知台日間有著這些齟齬、矛盾的存在。
現今台灣社會中許多人呼籲「台日友好」,日方則掀起「台灣潮」,台日民眾的交流變得頻繁多元,雙方的互相認識有相當大的進展,但許多人卻似乎刻意忽視或沒意識到相關的矛盾問題。即使針對對方的資訊和知識增加,若忽略那些思想、社會、歷史脈絡的分歧矛盾,在水面下雙方的意識齟齬不斷地增大,最後恐怕會「突然」導致無法挽回的破局。橫跨台日間的這些矛盾和齟齬,確實是極為難以解開的。但無論如何,至少必要的是,台日雙方民眾認識這種矛盾、齟齬的存在本身。
互相迴避「批判」的台日關係
約十九年前,我剛來台灣時,同事們給我一些關於台灣生活的建議,我還記得其中之一是「最好不要提及政治話題」。但我一直無視此勸告,時常聊聊政治、社會、歷史、思想相關話題,甚至十幾年後在台灣出書,內容都涉及「敏感」議題。讀者們必定會發現,本書含有對於台灣社會的批判意見。而我在書中到處痛批現代日本社會中的各種問題,有些讀者也可能會對此部分感到不愉快,因為部分台灣民眾似乎接觸到針對「日本」的批判,就懷有如自己遭攻擊似的情緒。
據我觀察,不少台灣民眾只關注日本社會中漂亮一面而迴避提及黑暗面向。例如,在我所任教的系所裡,不少同事時常批判地解釋日本的社會問題,但部分學生似乎將之理解為「系上老師們不喜歡日本」。「批判某個政治體制、政府、社會」與「厭惡該國家」截然不同,但部分人將這兩者混淆。此外,當我提到日本政治社會問題時,有時會遇上「此種論述讓企圖拉開台日距離的勢力得利」、「其他國家也有此問題」這種反應。我並非拒絕別人提出反駁,但那種說詞的背後,存在對於任何事情都從黨派、政治角力的角度來理解的思維方式。在這種邏輯下,實際存在著的問題本身和其受害者以及為改善它而奮鬥的人們永遠被忽略。
另一方面,由於對侵略戰爭、殖民主義的贖罪意識,二戰後許多日方人士有對於近鄰國家相當客氣的傾向。雖然近年來關注台灣的日本民眾大幅增加,許多人公然說「喜歡台灣」,但為台灣正面提出批判意見的人卻還不多。其實,我屢屢看到,在台灣旅遊或生活的日人諷刺地「評論」台灣,例如:交通安全太過惡劣;人行道無法正常行走;鐵皮屋和違章建築很多;裝在大樓外牆上的冷氣室外機看起來很可怕;店家倒閉後看板都不會撤除;到處都有錯誤的日文字;餐桌、洗手間不夠乾淨;有些食物油膩或太甜;時間觀念籠統等。那些人聊到這種無害無毒的生活相關話題時非常健談,嘴巴犀利惡毒,但一旦遇上較為「抽象」、「敏感」的政治社會議題,他們忽然就變得沉默寡言,或者直接模仿「台派」人士的口吻,只說出「台灣自由民主」、「台灣是個國家」、「台灣很可憐」等安全套語,令台方高興。
不過,我認為欠缺批判言論的「台日友好」,不能說是真正的「友好」。若台灣和日本真的要加強關係,就必須打造能互相坦承地交換意見的風氣。尊重對方是該有的態度,但永遠過於擔憂踩到對方國族情緒的地雷,始終迴避批判性對話,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賴關係。
做為一個日籍人士,我為何在台灣以中文發聲?
雖然如此,我還是無法完全否定日方人士不敢正面批判台方的情緒,因為即便殖民時代早已結束,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仍留下其後遺症,並且現在台日間仍有國家規模、國際地位等差別所帶來的不平衡關係。前提條件不平等且其原因中許多部分來自日方,在此情況下日方有什麼資格與台方「平等」地交換批判意見呢?
如本書中所述,現在台日間有語言方面的不平等關係。近來在日本,中文學習者人口大幅增加,許多日方人士在台灣積極以中文交談,但與學習日語的台灣人相比,其數量、比例仍然較低。並且許多台方人士似乎以為歐美白人和日人「較高級」,而內化「國際交流=英日語」的觀念,一看到歐、美、日人士就條件反射似地試著用英、日語交談。反之,許多日人雖然對於歐美白人懷有類似的觀念,卻認為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們以日語跟自己搭話是理所當然的。這種不平等的語言觀念和語言使用狀況,顯然是近代以後的「脫亞入歐」、殖民主義及其後遺症所留下的價值觀使然。
上面我談到台灣有迴避正面批判日方之嫌,但其實現在有不少台灣籍作家、記者、學者等,在日本媒體中以日語進行批判性言論活動。非文字工作者的民眾也在社群網站中向日方以日語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時發表相當嚴厲的批判意見,糾正日方台灣相關論述的問題。日方人士也許會以為台灣人擅長外語,對他們來說以日語說話是不怎麼樣的。但認真學習過外文的人都知道,在異國以其國家的語言發出批判意見,此行為會給予本人極大的心理壓力,哪怕你的講話或文筆聽起來或讀起來極為順暢,此問題都不可能消失。周圍都是當地人,只有你艱苦奮鬥地運用他們的語言對抗那些母語者,討論內容可能也會有你從未想過的當地社會文化脈絡,而讓你陷入出乎意料的窘境。平時向你示好的當地朋友們,一旦你講出批判意見,即使你遭攻擊且吃虧,說不定也不會幫你講話。雖然任何社會必定會有些人理解且同情這種苦難,他們可能會站在你那邊一同反擊對方,但你最後還是得自己應付落到你身上的子彈。最大的問題是,在當地社會中主導權永遠在母語者手上。
自日據時代至二戰後,許多台灣作家、學者、政治運動家等以日語從事創作、學術、言論活動,在(前)殖民地宗主國的平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的日文讀起來極為流暢,但他們卻仍不可能完全沒遭遇那種苦難,或多或少都在台日不平等關係所形成的逆境中搏鬥。反之,迄今為止,有多少日人在台灣的語言平台上進行批判性言論活動呢?現在在日本,中文學習者數量增多,對台灣的關注度也大幅提高。在台灣發表中文文章、學術論文等的日籍作家、學者、記者隨之逐漸增加,在社群網站中已有不少日籍網友以中文與台方交換意見。但總體而言,與以日語進行言論活動的台灣人相比,其數量和比例仍明顯為少,此狀況反映出台日間仍保留的不平等關係。
我之所以在台灣用中文書寫的原因,是希望對抗此情形。我認為,身為一個屬於前殖民地宗主國出身的人士,既然提出對於前殖民地社會的批判意見,至少要把自身投入到與當地人平等的平台上,在從前那些台灣日語作家們同樣的條件下進行言論活動。或許,以中文發表文章的日人增加區區一個也不可能推翻大局,但就我而言,這至少是一種如江湖人般的倫理意識,也是不願認輸的固執。我不願意在被日語防護膜圍繞的安全地帶中單方面批判台方,也不想輸給以日語跟日本主流社會堂堂正正對峙的台灣人士之勇氣。
剛遷來台灣時,我完全不會台灣的語言,日常生活都不如意,有時陷入出乎意料的困境。後來我的中文能力稍微進步,但現在還無法說是完美,當因語言障礙而陷入困難時,周圍的台灣人士幫助我。事實上,就我而言,中文書寫是對於台方的日語之「報恩」,但此「報恩」不可能是全面稱讚台方,因為「批判」就是文學家的生命線。此外,所有的批判性言論活動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才能成立的。本書中不少內容涉及針對台灣社會的批判,這是因為我現在身在台灣。但若我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社會脈絡中向不同的讀者層發表文章,我說不定會寫下擁護台灣的論述,以對抗當地的主流思想。
就我而言,「台灣」、「日本」算什麼呢?
讀到這裡,有些讀者也許會說:「做為一個日本人,你怎麼那麼關心台灣。」不過,請不要誤會,「日本人」並非我的身分認同的一切。我在日本靜岡縣東部鄉下出生長大,在茨城縣筑波市度過青春時代,而後搬遷到花蓮、台中。在各地遇到的具體人們、社會、自然風景、都市環境等,確實是現在構成「我」的重要因素,但「日本」各地的許多土地我沒親自踏上過,也不可能認識所有的「日本人」,並且在我人生中給予「我」深刻影響的人們中,有許多是外籍人士。對我而言,「日本」畢竟是個由各種媒體所打造的「想像意象、形象」,這雖然也算是構成「我」的因素之一,卻絕非一切。說到底,我畢竟是個個人主義者,我所寫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而我根本沒資格擅自代表全日本發言。
雖然如此,與外籍人士討論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時,我還是有肩負著某些歷史社會脈絡發聲的「責任」。日本和台灣之間有曾殖民/被殖民的特殊歷史,因此即使我自以為是個「世界公民」,但在台灣發表自己的意見時,仍無法逃脫做為一個日籍人士的歷史、社會責任。這種「國家自我認同」和「歷史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難以解釋,目前我無法以更明確的理論來說明,但在此我將這兩者區別開來。在本書中我有時會寫下「做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但這種句子與其說代表著我的「國家、民族認同」,不如說是「歷史社會責任」。
再者,我不敢說出「我喜歡台灣」那類句子。因為對我而言,「台灣」並非單純的遊玩、觀賞場所,也不是觀察、分析對象,而是我自己所生活的場所,它已經變成了構成「我」存在本身的核心因素之一,因此我無法以「喜歡/不喜歡」那種將事情單一化的說法談論它。我在台灣與各種人們相逢,經歷各類的事情,對此複雜多元的情緒交錯,實在難以言喻。並且我不可能認識台灣所有的地方、民眾。事實上,在日本生活時也有一樣的情形,因此我對於「日本」的感受也無法以「喜歡/不喜歡」來形容。
另一方面,我確實希望台日民眾能打造更好的社會。其實不僅台日,全世界所有的民眾本就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因為某種命運的捉弄使得我「偶然地」出生於日本,而後在台灣討生活,因此我接觸且思考台日相關議題的機會較多,並且做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我確實有義務該承擔某些歷史社會責任。我較為頻繁探討台日的理由,並非認為只有台灣和日本有出眾的價值。儘管如此,既然在台灣生活十九年之久,在我自身的生命中台灣確實有特別的存在感。對我而言,台灣並非用來加強自己的既有認識、意識形態之場所,而是充滿未知的「他者」之空間,它給予我機會懷疑自己既有的自明性且不斷重新打造思想。
拒絕「政治立場」的「文學」、「批評」
有些讀者也許會心中懷有一個疑問:「這本書的作者到底站在什麼樣的政治立場呢?」對此種提問我只能如此回答:「我的政治立場就是否定政治立場本身。」我在台灣頻繁看到或聽到「我的政治立場怎樣怎樣」那種說詞,但我對此懷有強烈違和感。所謂思想活動本來就是,藉由接觸他者讓自己的「學習/回饋」迴路起作用,不斷重新建構自我本身的動態過程,但「立場」卻讓這種「學習/回饋」迴路停駛,永遠讓人沉湎於固定的認知、意識形態的框架中。玩弄「此意見讓某某勢力得利」、「某某國家(政黨)也有一樣的問題」、「你們不能理解我們某某人的情緒」這類說詞的人們,只將保護自己的「立場」置於一切之上,且拒絕誠懇地面對他者和問題本身,停止「學習」、「回饋」的動態迴路。思想活動就此死亡,其言論變成如殭屍般的死板政治口號。不論泛綠/泛藍或右翼/左翼的差別,我都無法認同這種態度。
由於如此,我不打算將本書內容視作我的「政治立場」,也不會將之固定下來而死守它。各種各樣的社會議題陸續出現,我藉由思考這些重新打造自己的想法,不斷更新思想。本書就是,一邊面對台日相關政治社會文化議題、一邊不斷重新打造自己的思想,同時也將此過程本身與台灣的中文讀者們分享,這樣的思想言論實踐之動態紀錄。未來,藉由與讀者們的回饋對話,我有可能會反省本書內容的問題而改變想法。
最後我想解釋,政治社會議題對「文學家」有何種意義。我本來就是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研究者、評論家,但本書中許多內容卻與狹義的「文學」沒有直接的關連性。但在近代社會中,文學家並非只在狹義的「文學」中閉門不出的存在,而是總在扮演思考及書寫社會中各種各樣問題的角色。在許多國家中文學家都是這樣的存在,因此他們的作品總被要求含有與單純的娛樂不同的元素。
而近現代日本有稱為「批評」的領域,通常指的是文藝評論,但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柄谷行人等批評家,雖然以評論文學作品為據點或出發點,但同時也談論政治、社會、歷史、語言、哲學等涉及廣泛多元領域的問題,其社會影響力也相當大。現在,小說、詩歌等狹義的「文學」急速失去社會影響力,然而若將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視為一個龐大的「文本」,文學家仍有某種存在意義和社會責任。
在此意義上,在我自身的生命中,本書仍算是一本「文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