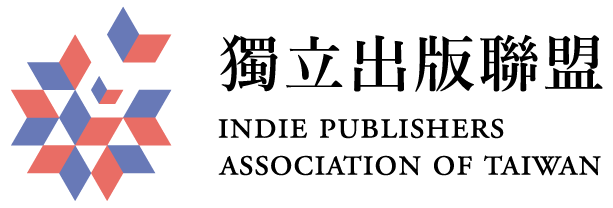十篇見證、改變臺灣社會的現場重磅紀錄,見證「民間力量」的崛起與壯大:暗無天日裡爬行、染病且災變致死的煤礦工,被消失三十年的綠島政治犯及其長年傷憂的家人,與鋼鐵搏命、為「世界第一」死去卻無聲的拆船工,因愛國獎券而興的大家樂、集體瘋發財夢的地下經濟癲狂圖,戒嚴時代在總統府高舉「怨」字、帶起民間環境運動第一波的鹿港人,將桃園機場事件暴民還原為人、照見兩黨政治外的群眾實像,淹沒在經濟發展至上主義、遭受石化工業罔顧棄置的林園漁民,……
身為冒險採訪核電廠員工、暴露台電內幕的反核吹哨者,更是領頭舉辦反核運動的第一人──文學可以改變世界的實證者楊渡,前進到下層世界,目擊真實的群眾生存實貌,聽見在地的聲音與憤怒,寫下那些受無路可出現實挫傷的人們心中的巨大哀痛與絕望。
篤信「沒有現場,沒有真相。」的文學家楊渡,親眼所見親身所感,深入苦難的第一現場,直擊「現實,竟然比想像更恐怖。/現實的一切,竟超出一切文學、藝術的想像力之上。」從而描繪暗夜中的美麗黑靈魂們,與諸多邊緣分子同在,報導底層社會的血汗,書寫在地生活的豐饒細節,並體現最可貴的在場精神,驗證人性之光、文學之心。時隔多年,在激情過後,楊渡回頭審視一九八〇年代的人心、群像,辨識彼時的樣貌與侷限,既是記錄臺灣社會轉型的繁複現象,同時為時代重下註解,更可供當代各類運動作為借鏡與警醒。
本書特色
「只要是為了生存而奮鬥著、艱辛著的人類,我想,每個人都是莊嚴而神聖的。」──楊渡
在時代的激情與喧囂消散後
回望現場──
一個時代的誕生,一場史詩般的告別。
楊渡以充滿時間差的報導文學
復還一九八〇年代。
獻給所有在「暴雨將至」年代中,迷惘、追尋、衝撞,卻又充滿希望的靈魂。
■ 第一手報導者視角,記錄社會巨變現場:
由1980年代活躍於第一線的新聞記者撰寫,忠實呈現拆船工人、礦工、反核青年與街頭示威者的聲音與處境。
■ 融合文學與報導,描繪人性與歷史交錯的場景:
文筆細膩,兼具田野採訪的真實與文學筆法的深情,讓歷史不只是事件,更是生命的肌理。
■ 見證民間力量如何推動臺灣的轉型時刻:
從解嚴前夕的社會力崛起、環保與反核運動,到街頭的抗爭與禁書的傳閱,本書全面呈現臺灣走向民主與現代性的基礎。
作者簡介
楊渡
詩人、作家。喜歡旅行、閱讀、電影和足球。最喜歡的地方,是新疆和阿爾卑斯山。大山大水,以及無盡的沙漠。最喜歡的電影是《直到世界的盡頭》。
生於台中農村家庭,寫過詩、散文,編過雜誌,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主持過專題報導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與世界共舞」等。其著作《未燒書》獲第34屆梁實秋散文大師獎首獎。
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報導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激動一九四五》、《紅雲:嚴秀峰傳》、《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大學的脊梁:臺大校長遴選事件與管中閔心情記事》、《暗夜傳燈人》、《我們如何記憶這時代—報導文學十三講》;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短篇小說集《九天九夜》;戲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以及歷史紀實《有溫度的台灣史》、《1624,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澎湖灣的荷蘭船》等十餘種。
目錄
序文 狂.飆.一九八○
一 臺灣錢淹腳目的年代/瘋狂大家樂
二 綠島囚禁三十年
三 礦坑裡的黑靈魂
四 血肉築成的拆船王國
五 媽祖廟的香火,點燃社會轉型的火種
六 機場事件目擊日記
七 天火荒原
八 深度探訪核電廠
九 恆春/臺灣反核第一夜
附錄 蘭嶼反核,第一聲
序文
狂.飆.一九八〇
經過長長的四十年的時光隧道之後,
我們回望,才想起隧道中,
我們曾在幽暗中吶喊,眾聲喧嘩,回音盪漾。
當我們走出那長長的隧道,
眼睛迎向逆光的瞬間,
世界忽然白茫茫一片。
那是強光的盲目?
還是失去方向的茫然?
我們如何找回最初那一顆熱血之心?
談起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我們總離不開幾個鮮明的字眼「臺灣錢淹腳目」、「自力救濟」、「咱要出頭天」、「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兩岸探親」、社會力解放」……,諸種標誌。
然而,當我們回望,我們真的了解一九八〇年代嗎?在那些表象之中,隱含著多少社會矛盾,多少經濟狂飆,多少人性扭曲,多少結構性變遷,多少人的命運的上升與沉淪……。
那是臺灣成長為「大人」前的青春躁動?還是老朽威權要死亡之前的最後掙?是轉型的大陣痛?還是時代要新生必然的掙脫與奮戰?
一如二〇二二年底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的〈狂八〇: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所標舉的特質:狂、狂飆、反叛、打破禁忌、前衛實驗、混種翻譯……,那是一個難以單一定義的年代,也是臺灣社會巨變的年代。
然而,除了戒嚴解嚴,除了狂飆破禁,我們真的好好的凝視過它嗎?我們是否曾認真思考過它的深層結構,更重要的是,從更長遠的大歷史觀點,一九八〇年代在臺灣史中,到底代表著什麼意義?在一九七〇到八〇年代的經濟起飛之後,這一系列的社會運動、體制衝撞、解除戒嚴等現象之上,我們要如何定位一九八〇年代的意義?
回到每一個人的自身,一九八〇年代是許多人成長的歷史,讀書、考試、解除禁忌、開始戀愛、看黨外雜誌、臺大前面書攤上買三十年代禁書、站上街頭、示威遊行、在路邊攤喝酒、在新公園(註1)約會……。
和我們的生命如此深深關連著的這一段歷史,我們可曾再次凝視,深情回望?
當我們回望,我們能不能看清楚來時的道路,而不只是白茫茫的強光?
一,打破禁忌的年代
談起一九八〇,我們總是最先想到一句話:「青春!狂飆!」
狂飆,最明顯的標誌是:飆車族。
從南到北,從北投的大度路,到臺中的中港路(註2),從梧棲濱海大道,到高雄工業區新建大道。一群年輕人,青春熱血,無懼生死,無視於時速限制,無視於沒安全帽有多危險(當年尚無騎機車戴安全帽的規定,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開始實施強制戴安全帽之立法),無視於有無違規,無視於警察的規勸取締,不僅當場飆車競賽,甚至和警察飆車追逐,比賽誰技術更好,誰有能耐甩掉警車。而警察當時開的都是國產車,根本不足以和進口車、越野跑車、改裝車、知名賽車相比。
狂飆,也顯現在金錢遊戲。大家樂是地下經濟的典型。跟著愛國獎券開獎,用其號碼為依據來賭博的大家樂,每一期約十天之內,至少四、五十億金額在全臺灣流動。民間游資多得地下經濟比地上投資更兇悍。所有法令都是舊的,它只能規範到舊的經濟活動,對新興的地下經濟活動,諸如地下投資公司、集資標會、非法賭博,卻毫無辦法。
地下經濟也顯現為野雞車的盛行。由於大量勞動人口向城市流動,每到假日便是返鄉狂潮,限定由公路局運行的高速公路只有國光號和中興號,根本不敷所需。民間自行營運起來的野雞車大行其道。南來北往,比國營的公路局更方便。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檳榔攤,小小的雜貨店,自動自發的加盟,成為野雞車的售票點,上下車的地方。
急速積累的金錢,瞬間暴富的地主、暴發戶,也帶來扭曲而擴張的「俗擱有力」的欲望。地下酒家在城鄉之間,大行其道。
鄉村酒家自有它的客源與經營者,以及女性的陪酒者。原住民部落的未成年少女被人口販賣到陌生的都會,站在都市的暗巷裡,關在鐵柵欄的後面,向城市揮舞著招來的手,卻更像是無助而悲哀的控訴。
當時的流行文化現象也生猛有力。一九八五年左右,卡拉OK 開始大行其道。原本戒嚴時代的法律對歌舞廳有嚴格規定,得持有八大行業的執照才能唱歌跳舞營業。但在一九八五年之後,任何一家餐廳,只要有卡拉 OK 設備(發源於日本,引進後在臺灣改進為本土歌曲的伴唱帶),誰都可以上臺唱歌。來賓只要先點唱,餐廳排歌的服務生自會點名幾桌來賓點唱某一首歌。白天經營簡餐西餐的小咖啡館,晚上化身為卡拉OK的店。一支麥克風,一臺點唱機,就是飲酒歡聚的場所。雖也有各桌來賓之間點了同一歌,搶著上臺而有點小糾紛,但也可以合唱同臺,同歡共樂。
而新興的伴唱帶(這古老的名詞,意味著一種錄音帶似的伴唱帶,一卷約有十幾首歌,依來賓點的歌來播放),也是隨著臺灣的新興伴唱設備而生產出來,國、臺、日、英語都有。流行歌的主旋律也改變了。那些夜市街頭賣的卡帶,傳唱的歌,變得比電視臺傳播的更快,更大受歡迎。
沈文程的〈心事誰人知〉就是從臺中的歌廳、夜市市集、再到卡拉 OK 伴唱,風靡了全臺灣。民間的庶民流行文化取代了過去由三臺公營電視所控制的歌舞系統。夜市與卡拉 OK 的力量,形成一九八〇年代生猛的大聲歡唱吶喊的風景。
而卡拉 OK 伴唱帶的出現,與伴酒歡唱的女子(她們何曾不是流動於城鄉之間的另一種流動的風景),一樣在城市與鄉村,鼓動著浮誇的慾望城國。
各種各類的地下活動,上自地下金融機構在民間吸收游資,股市開始飆升;下到機車、汽車改裝飆速,地下營運的加油站、野雞車、兼營色情的小吃店,從城市到鄉村,處處流蕩。在在都說明了一個事實:急速發展富裕起來的經濟動力、大量的人口流動,社會新興的動能,其能量已超出舊有體制所能規範的框架,更遠遠超出了政府的公營機構的交通、運輸、金融、銀行、股市等,所能提供的一切。
各種新興的社會活動因應時勢,自發崛起。那種感覺,就像一個少年茁壯成長,早已是體格壯碩的青年,你卻叫他還穿著小學生的制服,唸著小學生的課文一樣;事實上,他的肌肉,早已撐破了那小小的制服;他的身體,早已成熟為青春欲望的肉身;他的腦袋,早已充滿賀爾蒙的衝動與欲望。
政治也是另一個急速成長起來的軀體。
一九八一年臺北市議員選舉是黨外新生代崛起的關鍵時刻。林正杰以「黨外長子」的使命自期,以「正的、長的、扁的」(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聯手當選,繼美麗島受難者家屬的參選(周清玉、許榮淑)之後,開啟新生代參政的風潮。隨後林正杰辦了《前進》雜誌,而許榮淑則辦《深耕》(註3)與康寧祥的《八十年代》共同開創黨外雜誌的新時代。
由於民間需求旺盛,一九八〇年代初,重慶南路的書報攤上,出現了大量的黨外雜誌,有些被查禁的雜誌,反而賣得更好。書攤的老闆把禁書藏在報攤下方,如果看到你在翻看黨外雜誌,再觀察你不像來查禁書的特務,便會從底層抽出禁書,故意現一下即收起來,說:「這是剛查禁的,要買要快,再不然被沒收就沒有了。」大部分有興趣的人也沒有時間翻看內容,帶著一種偷偷摸摸,怕被發現的快感,很快付了錢,用報紙包了書,便帶走了。
而在臺大附近,本有許多書店,大家眼看禁書有銷路,便也印起了另一種禁書。在新生南路附近的書攤上,開始出現沒有寫作者名字,或作者寫了另一種筆名,或本名的書。例如:魯迅的小說,書封的作者名叫「周樹人」;巴金《家》、《春》、《秋》,書封寫的作者叫巴克,因他是彼得.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者。其他如錢鍾書的《談藝錄》,現代詩選等等,也都不知被哪一個學校的學生或書商給印了出來。大量的一九三〇年代的禁書,從沈從文、魯迅,到巴金、冰心、茅盾、乃至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有。
那是一個衝破禁忌的時代。閱讀打開了視野,也打破了各種思想禁忌。那是一個知識補課的時代,把過去禁忌的文化補回來。
從禁書到雜誌,從交通運輸到地下賭盤,從路上飆車到封路賽車,乃至於後來的反杜邦運動,帶領群眾走上鹿港街頭,搞出了美麗島事件之後的第一場群眾遊行。這一切,都是在破除禁忌,向權威挑戰。那是充滿豐沛的民間力量的時代。
當時有諸多議論,認為那是要衝破體制,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開端。但另一方面,也有諸種壓力,要求維護社會秩序,不能任由民眾「脫序」(這是當年批評者最常用的古老名詞)。
各種禁忌與開放交會的年代,人心充滿迷惘、困頓、追尋、衝撞,卻又充滿希望。
我當時曾參與主編過黨外雜誌,也曾主編反抗的文學詩刊,每一期都被查禁。內心卻充滿「要來一場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的激情。以極度的熱血,想衝破戒嚴的羅網,走向民主自由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