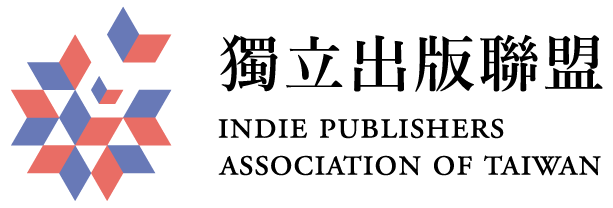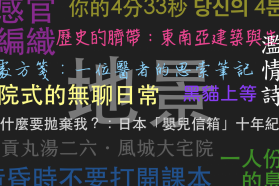感官編織
Distributor:
Publisher:
Publishing Date:
ISBN:
Format :
Category:
Price:
二〇〇五年起,詩人宛璇開始往返法國與臺灣,幾年後,選擇返臺定居。這期間生命歷程的流轉、生活的選擇,以及與所處環境的對話,自然地反映在書寫中。
這本詩集的最初雛形是二〇一五年夏天,對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一年間的文字進行首次選編。爾後其它因緣匯聚,宛璇決定先出版母語親子活印有聲詩集《我想欲踮海內面醒過來—子與母最初的詩》。直到二〇二一年——距離詩集中最後完成的詩,也已相隔十年,它才真正地以一本書的形式開始被完成,並加入了同一時期間的圖像創作。過程中,詩人階段性地重讀,刪減,一遍又一遍,直到其中大部分,都似乎脫離她的個人生命,成為一個個擁有自己影子的他者:
部族的先人/我們什麼都看得到/我們什麼都感覺得到/棉花要成為細線/而細線要成為布匹/將那已被完成的遺忘吧/另一個事物,已然現身
(來自印尼松巴島語)
本書特色
*來自二〇〇五-二〇一二年間的詩與圖
「波赫士形容人類的文字『貧乏而野心勃勃』,但宛璇的詩卻彷彿另闢蹊徑,來到了文字的另一面,那確實一如詩集的名字《感官編織》,色聲香味觸法,將每種感官推展到極致,圖窮匕乃現。」/詩人隱匿專文推薦
所有神祕的腳步都朝向命運。站著睡站著作夢
站著聽床邊故事。把讀和聽的人都丟進故事正中央
時間進不去那棟房子,時間的犬齒。與未知通信,
向海游去一座無名的島。
黃昏打壓過來,沒有夢的陌生人
作者介紹
蔡宛璇
出生於春天的群島。喜歡畫畫閱讀看雲看海的小孩。學習視覺藝術同時自己寫詩。在大島臺灣畢業後,去歐陸七年,後回到大島——生活,與從事當代藝術創作相關工作。出版詩集「潮 汐」。和聲音藝術工作者Yannick Dauby在臺成立「回看工作室」,繼續藝術相關活動。成為母親,慢慢講回母語——臺語。出版《陌生的持有》詩圖集。嘗試寫臺語詩。第二次成為母親。出版活印親子母語詩集《我想欲踮海內面醒過來—子與母最初的詩》。繼續創作、周邊工作、編織生活。
目錄
推薦序 趁亂告白——序宛璇詩集《感官編織》/隱匿
卷一 正常地滾動
(正常地滾動)
(緩慢)
生與活之溢出
穿 雪 花
小雪
冬燼
今天
行進中,MRT
六四晚上我們讀詩
睡
家寒害
閏午夜
鴞喚
(在秋天)
卷二 地中海北
小白狗
Valberg 漫步
Lac du Beuil
地鐵
老西蒙娜
秋天的支流
搬家路間小憩
路上的詩
槲寄生
卷三 K
Cher K et H et P
上路之前偶得
報春給 K
K—冬小調
他讓我看到
影子初夏—給在某處的 Y.
夢中生活:回訪
壞小孩
(親愛的 P)
她她
(K,)
卷四 異土
沿岸
沿岸—恐懼之邦
岩燕與夜鷹之間
Ahja jõgi
賽拉耶佛的果陀
卷五 沙數
洪荒的開始或斷裂的最初
((哎)))
也是,情歌
沙數
夜裡的水鹿
在漫長的徒步旅行後
卷六 感官編織
有河蒼鷺
電影院內外(頤和園後)
Jouhikko 的風
Il a disparut dans un silence total 它消失在一種全然的靜默中
巴卡(Baka)
宅夢
年節
移動中的幽靈
Caroline B. ,你的圖我的懂
安迪與沃荷
從水出發的一場不連續演出
餵房子吃夢的人
幽靈化的感官
卷七 脈
(大樓)
(勞工節黎明, London-Nice)
年代蒼茫擁擠
偽螢火蟲
因緣
暗下之前
短歌
莫可名
涯
野島(母親節記事)
船破圖三個彎,轉給白海豚
空隙
後記
推薦序
趁亂告白——序宛璇詩集《感官編織》
隱匿
猶記得二〇〇七年的春天,宛璇帶著一抹笑意,從樓梯間浮出有河書店水面的那一刻——明明是初次相遇,我卻打從心底發出了奇異的共鳴——那種感覺不是一見如故或者失散多年的妹妹所能形容的,那幾乎可說「她是我失落在另一世界的一部分」或者「我是遭遇病蟲害之後的她」;那就像世界是一巨大的生命體,我們本來生在同一棵樹上,只是她往陽光的方向盡全力伸展綠葉昂揚的枝椏,我則向著陰濕的地底潛入,試圖將根鬚深入地心。
或許因為初遇的震撼吧,我做了幾個有她參與的夢,其中一個至今仍歷歷在目。夢裡我和宛璇都來到死後的世界,生活於深不見底的雨林裡,在樹冠間穿梭飛越,各自修習不同派別的武術,且在挫折中不斷精進。後來宛璇告訴我,我做此夢的日期正巧是她的生日。
儘管有這樣強烈的似曾相識感,宛璇卻是當時剛開書店的我從未見過的異種生物:她事事關心、樂於學習,為各式各樣的藝術和音樂而傾心,且彷彿外掛了外星人的接收器,能察覺極細微的聲音、辨識出最黯淡處的微小變化,觸覺想必也異常靈敏,你只要看過她用一支細筆在紙上擦掠,那附魔般的筆尖移動,顯然正在將彼時所感知的無以名狀之物,從指尖輸送出來。
除此之外,當時必須留守書店的我,也挺羨慕她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因為那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所在,而非有名的觀光景點。但我並不覺得遺憾,因為我有幾位這樣的朋友,他們代替我去過了那些燦爛美好的所在,而我則透過他們的創作,一一接收到這些來自宇宙邊緣的神祕訊息。
奇怪的是,雖然我喜歡宛璇的詩且已將這本詩集讀過數遍,卻無法像其他喜愛的詩人那樣記住某些詩句,甚至能背誦或隨意引用。當我嘗試從腦袋裡召喚出宛璇的詩句時,浮現的不是文字,而是許多畫面、聲響和氣味——從塵埃堆積的破碗裡滿溢出來的老宅之夢、大黑暗的森林中水鹿濕潤的眼睛、在如潮的月光裡搖蕩著的群島、終夜吹送的褐林鴞的聲音、沿著我沒去過的湖畔四周冒生的冷又安靜的青煙——這些詩,彷彿脫開了文字,成為其他的……其他的什麼呢?
回想那些我能背誦的詩,它們都有渴望表達的洞見、有情節和感情、讓人毛骨悚然或者激動落淚,然而我最喜歡的宛璇的許多詩作卻並非如此,我無法用文字記憶,而必須回到詩行間,如此便能再一次地感受;那感覺就像一方面睜開眼睛閱讀,一方面卻得閉上長年以來學習文字的慣性之眼,我必須交出自己,全身全心潛入那個閃耀著幽暗波光的異世界,於是乃能觸摸與傾聽。
隨意舉例:「草叢中被夏天打動節拍器蚱蜢的腿翅映滿光」、「泥土蒸氣,殘翅落枝,薄荷與青苔/不是綠的綠,和幾乎不存在的黯系」、「映在石壁上波紋形的意念」、「海綿吸滿夜色,在海床上/傾聽漆黑巨大無邊」……等等,這些描景、微物的陳列,顯示她只願忠實地呈現與讚嘆,而無意取為己用,卻也因為無所求(甚至忘卻自己正在寫詩),而其中有神,於是成為無法背誦的文字。
波赫士形容人類的文字「貧乏而野心勃勃」,但宛璇的詩卻彷彿另闢蹊徑,來到了文字的另一面,那確實一如詩集的名字《感官編織》,色聲香味觸法,必須將每種感官推展到極致,圖窮匕乃現。
我不敢說她的詩是最好的,因為「最」與「好」,甚至「詩」,都帶有評判和規範的意味,我只能說,同為詩的習作者,我很受觸動與啟發,也很感激宛璇是如此誠實,她沒有試圖將這些生動地捕捉而來的光,「構造」為一首「完整」的詩。當然也不排除她為了留下這些光,費盡了苦心,直至它們看起來渾然天成,比如這一小段就似乎透露出勞動的痕跡:「為了得到治癒/他必須起身/去尋回/那而今四散曠野/卻曾被召喚過無數次/的語言」。還有底下這首,短而帶著棒喝的力道,我感覺自己也在此詩中得到了校正,回到本該屬於我的運行軌道:
我被這些無名的樹所包圍。
它們無法為自己命名。但太陽昭示著它們存在
的中心。而它們
則昭示出我存在的路徑。
當然,除了短詩,宛璇也有結構完整的長詩,甚至有組詩,但這些詩仍維持住她獨有的靈光。就如顧城說的,有些詩是「長」出來的,有些是「寫」出來的,詩人終究不是靈媒,不能完全依靠詩句自動長出,多數時候仍然必須排列字句,為了無法找到的那個準確的字而苦惱。宛璇這一類寫出來的詩大概是與社會議題相關,或帶有批判性的作品,儘管這些可能不是我的最愛,但還是十分動人,比如為反國光石化而寫的〈三個彎,轉給白海豚〉,讀到最後,不禁鼻酸,因為宛璇彷彿化身媽祖婆,將同等貴重的白海豚與金孫,一同攬進溫柔的懷抱裡:
母親正用新買的十元大紅塑膠桶
為她的寶貝金孫
細細溫柔
洗淨身軀,啊……
向晚的風
從海上來手心手背。
手心手背,心肝寶貝。
而我也非常喜歡她散文形式的詩,比如寫老房子的詩,那少見的對於空間的敏感和呈現,彷彿每個字都堆積著灰塵和歲月的重量:「四十年後有個人,穿過夏日銀合歡和野釋迦樹婆娑的天井,進入這間屋子的夢裡。」、「風在那些房子的周邊,不停兜著圈子。它撞擊緩慢支解中的木門,吹奏死去珊瑚群的骨骼縫隙,風化中的玄武岩廊柱,布滿孔洞,兩旁拼命搖晃著的木麻黃,整排整排在戳動天空。/天空灰白蒼茫,海在風來的地方日夜翻湧。」……還有底下這首,將她對人造物的譴責與生而為人的愧疚藏起,彷彿僅是一則遠遊歸來的遊子,對母土的跪撫與親吻:
這片國土北方唯一的原始林彰顯出「體」,
而非各式居住其中的生命。這是人造林所不知
道的世界。
在子夜離開了草原去侵襲沉睡村莊的沼澤之
霧,也在說著類似的母語。
即使是人站在那裡雙眼緊閉,即使是想要說而
說不出的攝影機。都無法精確描繪出,
這先在的風景。
我想著自己之所以受觸動,應該是彼此有許多共通點,而我之所以受啟發,卻是因為她對我來說仍是不可解的謎。比如我始終無法理解,她為何能在知悉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之後,仍對人世懷抱熱情、善意與好奇?她恆常將感受的觸鬚往四周伸展,不害怕因為敏感而受傷;她對充盈於生活中的美善滿懷感激,創作渴望同時來自宇宙和內在的核心,她僅僅遵從於此,不在意最終呈現的方式為何,於是她才能跨越各種領域:詩、畫、裝置藝術、聲音、影像……甚至以破臺語發表反對澎湖博弈的演說(當時我笑得在地上滾動);學習法語、臺語、原住民語;和伴侶攜手至荒野鄉野間錄音,或在城市的美術館裡佈展;堅持環保,所以她總在巨大的背包裡塞滿水壺、餐具、便當盒等等;同時她也和兩個孩子一起種菜、做飯,且在備料時,偷偷為一顆紫洋蔥的剖面結構之美而感動不已——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宛璇。
寫到最後,我突然意識到,或許現世即是我夢境中那個死後的世界?於是根據柏拉圖,儘管靈魂的雙頭馬車仍未馴服,但因我們曾見過雲端上的世界,那裡是我們的所來之處,因此,不管這個世界有多麼糟,我們必能看穿變動與虛假之物,而我們的眼,將僅僅注視著永恆的事物,世界的本質。
底下是在閱讀中意外長出來的一首詩,獻給她。
所來之處
在緩慢的閱讀中跋涉
如一荒闊無邊的夢
我不由自主地想著
如果不是遭遇嚴重的病蟲害
你是我本該長成的模樣
而生命是
一
龐大的集體
我們是其分岔的枝椏
你向陽而伸展
光與水分子沒入
潮汐
曾經陌生的持有
接續著從海裡醒來的
感官編織而我則將根鬚深入
另一片天空
以真菌封存
星塵
然則時光往復
鏡照如一微中子
穿過整個宇宙仍未
遇見彼此
於是你手執幾縷
發光的線條
沿路拾來幾顆黝黑
沉默的字
讓風遍流其中
一支多孔洞的樂器
要我們向著所來處
閉眼
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