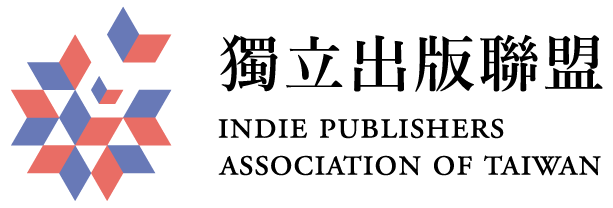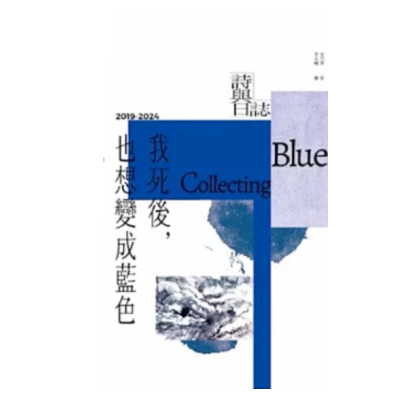
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2019-2024 詩與日誌
繪者:
經銷商:
出版社:
出版日期:
ISBN:
規格 :
分類:
定價:
小寫全新書系:寫日記
安撫、療癒自我的修復之旅
*旅英香港作家鍾耀華、精神科醫師、醫療人類學家吳易澄專文推薦
*香港藝術家、獨立音樂唱作人曾永曦插畫
*《流離之書》作者金其琪人生劇場之「後臺」,剝除外殼,袒露自我之作。
在多年的籌備後,小寫推出全新書系:寫日記,首發由《流離之書》作者金其琪於2019-2024之間所記下的日記與詩,名為《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日記作為紀錄的形式,一向具有私人史的歷史意義,在近代人文社科與心理學之中逐漸受到重視;而「寫日記」本身,具有拆解、拼貼、拾起、聚攏,將看似連續的日常切割成碎片,復又將碎片聚合成具有意義的片段之意。透過日記,個人得以召喚經驗主體,並與之對話。
在本書寫作的五年中,金其琪透過不間斷的創作日誌、詩歌和散文,從未停止與內在的自我對話,往文字深處去,為的是為痛楚、痛苦、受苦、憂鬱、創傷等等經歷與情緒,尋找一個更適切的名字,更貼近真實的說法。如書中所說,放置它們唯一的方式就是寫下來。寫下來,如同船舶在大洋中下錨,錨的鉤子深入海底,漂泊無定和隨波逐流的人,才暫時找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本書推薦人吳易澄引用伊朗裔人類學家奧基德.布勞珊(Orkideh Behrouzan)在民族誌《百憂解日誌》(Prozak Diaries)裡頭的一段話:「有時,我們會採用那些能夠撫慰我們、並幫助我們理解經歷的語言(例如精神醫學的語言),這些語詞能減輕不確定與羞恥的重擔,而某些語調也最能投射我們的渴望。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語言、語調與沉默,會逐漸改變我們理解我們的故事、包括我們自己,以及這個世界如何持續運行的方式。」這是語言和文字的力量,也是書寫和敘事的力量。
作者簡介
金其琪
記者出身的寫作者,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生。北京四年,香港四年,臺灣第七年。作品獲多個新聞獎,著有《流離之書:跨界移動紀事》、合著有《抵達安康》等。現任端傳媒特約編輯,個人工作室 Kiki and Co. Studio 籌備中,探索小誌、植物拓印、田野錄音與煮食。小貓咪「馬桶蓋」的姐姐。
繪者簡介
曾永曦
出生於香港,從事視覺藝術及設計,也是獨立音樂唱作人。他的不少作品曾在各類媒體和展覽上出現。創作愛游走現實邊緣,風格傾向抽象,亦帶隨意即興。音樂方面受到早期爵士、民謠、搖滾及電子影響。曾與劇場、舞蹈、詩歌和電影等不同界別合作。共出版了兩本故事圖書和五張音樂專輯,包括:Traces and Entanglements (2024),Whale Song (2008),Little Cold Red (2005),The Adventure of a Small-Headed Turtle (兒童圖書,2012)和 Twelve Tales in Eleven Monochromes (短篇故事,1996)。
目錄
推薦序 如果有的話,在哪裏?/鍾耀華
推薦序 養貓、煮飯與寫字:序寫金其琪的憂鬱紀事/吳易澄
2019-2020 永劫不死的方法
2021-2022 不可能的家
2023 靈魂的碎片
2024 一個擁抱撐起的世界
後記
推薦序
鍾耀華
如果有的話,在哪裏?
——在生生死死明明滅滅的動蕩時代保有記憶的碎片,帶著意識直面恐懼,創造回家的歸途。
降生於這個星球,面對環境變遷生命流徙,靈魂被囚禁,在有形的肉身軀殼,在抽象的思想矩陣。清晨的陽光灑落,穿透露水折射輝煌,映照在我們的臉上,我們渴望,我們期待,想要離開的念頭又反覆搖晃,仿彿時間錯位,人類形體外框的背後裂生出過去的自我——來自前世的、今生的,透過母體與家族,從過去的、現在的延展到未來。不充分的,挫傷的,地方的,人際的,無法與之和解的。於是停滯,遲緩,斷裂,於是愛無能,身上有這麼多能量,仇恨與憤怒卻占據了身心靈。我們不甘,瘋狂想要做些甚麼,欲望滋長,強劇地體驗,希望身體被狂暴的悲哀與喜樂振動,確認內在脈搏仍舊跳動,證明自我仍然活著。
我認識金其琪於二〇一五年創辦的端傳媒,當時我們共處一個辦公室,屬不同組別,基本上沒甚麼交疊。直至後來,我離職了,她離開了;她到中國,又去臺灣,而我在香港,又到臺灣,最後抵達英國,我們不算深交,聯絡都少。
但每次見到她,我都從她的眼裏,看到和自己相似的哀愁與痛,想像死亡與逃離的渴求,和某種生之努力。仿彿某種精神在隱微處,某組密碼對上連繫,某個空間擴展了。
我從沒告訴她這種感覺。
這本書寫下她的內在狀態,那些起伏,無解的自傷與掙扎,關於知識與人生,關於愛,關於記憶,寫的是香港,是中國,是臺灣,是疫情,是家庭,是貓咪,是情欲。每個人無非是經歷一些事故,事件,持續拉扯與糾纏,生命被拖進無底的沼澤,但從中可以生出力量,一點一滴地理解自己,拾回自己,理解他人,理解社區,理解世界。用其琪的說法,不過是「珍惜生命在給定的秩序外溢出的窸窸窣窣」。
很高興她出版這本小書,她說Love is still there,其實愛是絞不碎的。我說愛從未止息。她說也許自己就是要靠近風暴眼,才可以離開風暴。我說我們與自己的故道有時差,曾撒下一列如水的凱歌或悲嗚,全然的臨在引領我們穿越如河流的時間觀念之障,看見曾經的經驗與行腳被時光照出不同的影子,有深淺有長闊有高低,貌似統合於一身的記憶幻化為雜蕪的荒地,當光照轉動,所有又遙遙如霧散不復再。又唯有如此不斷往返,我們明白活著的不必如此,不追求於盛放,不執傷於凋零,重新發現道之為道。
閱讀她的日記文字,那些日常的呢喃絮語,就像邀請自己回到那輕柔又易傷的內裏,那個如初生對一切好奇又期待被愛的嬰孩,請求愛護,請求他人的關懷,請求大家多和自己說話。我們都是如此長大,我們仍然可以創造,不也因為別人愛的饋贈嗎?愛就在周邊,收獲這份珍藏,將愛輻射開去,就是最好的報答。
「想要感到自己活著」,是因為裡面還有生之渴望,有些栽種了是不會死的。仍然活著本身就是奇蹟,是以肉身形態活在現世裏,最美麗的豐收。本書書名叫《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我問她想傳遞的是關於死亡嗎?她說重點是藍色,是blue是憂鬱,至於憂鬱了要不要去死,那是不一定的。她說她想傳遞的可能是一個人如何憂鬱又活下來吧,但是並不保證能活多久的那種。豐收過後仍然能夠收成嗎?我們都不知道也無法肯定,但至少先感謝成就當下的全部,享受慶典。至少我在她的文字裏,找到某種堅持自己的微小力量。謝謝她邀請我作序。
個人即整體,並非只有你,只有我,只有她,只有他想要家,想要有理解,想要有陪伴,「你看,我們就像珊瑚礁一樣,每一顆都不一樣。海洋和島嶼的生活智慧早就告訴我們,不一定每個人都要被打磨成方方整整的一模一樣,也可以彼此疊在一起,鑄成一堵牆。」每個看來不夠認真不夠嚴肅不夠普遍的幽微重覆的獨白,都不必如是,穿過迷霧障眼,我們持續寫作,繼續表達,依然相信,將得見山海,看到彼此在遠山大海裏,在為相同的夢編織。
「和所有的創造一樣,物質需要浸潤在精神之河,由此誕生生動的靈魂,散發著意識的輝光;當意識黯淡,創造性也會隨之消失。只有從無時無刻不在試圖侵蝕我們的陰影——『非存在』那裡汲取,持續地創造,才能保有我們對外的掌握權。因此,光是『看』這個行為,比如看山,滿懷滲透性的愛去看,就能在非存在的浩瀚空間裡拓寬存有,而這正是人類存在的唯一理由。」——《山之生》(The Living Mountain),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管嘯塵譯,新經典文化出版。
是為推薦序,在英國布里斯托。
2025.07.06
耀華
鍾耀華|
寫作者,在現世尋找生之意義。
推薦序
吳易澄
養貓、煮飯與寫字:序寫金其琪的憂鬱紀事
起初注意到金其琪的作品,是在端傳媒上的阿美族祭師的報導,說的是學者巴奈.母路的身分轉變,從學術世界走入部落文化實踐的故事。而後再次吸引我注意到的是在她的非虛構書寫著作《流離之書》裡的一篇〈中國醫護疫情後心理創傷調查〉,正巧對應了我在COVID-19疫情期間進行的研究,於是我邀請其琪組成了一個議題小組,至韓國大邱參與亞洲研究會議,針對疫情間的創傷議題進行報告。會議期間我才知道,其琪另外安排了一個採訪行程,到首爾採訪了李滄東,那位時時叩問著韓國底層小人物的人性、認同與存在的導演。從這些書寫的路徑來看,金其琪看似有種雜食性的知識攝取與生產,然而也不難看出她所凝視之處,無不是受壓迫者、流浪者、邊緣者在世間掙扎的角落。
出身於中國浙江溫州,然後至香港讀書,輾轉來到臺灣求學,這個移動過程並非是一個尋常的軌跡。其琪在離開記者工作之後(其實也沒有真的離開),轉而投入了人類學的領域學習,她持續關注的是香港人的離散與創傷,並且持續參與在某種集體創傷的重構與創作過程中。曾經在香港求學的其琪,必然也見證了那段國安法實施前後香港社會的轉變與痛楚。這本冊子所記錄那些身體的、心理的痛苦,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有時候,那些文句採取的是極為直白的語言,有時候,卻採取了隱晦的詩句。這種風格上的不穩定,究竟應如何理解?
我想起多年在大學參加詩社的往事。那是一個名為「阿米巴」的詩社,在加入詩社時便明白那不只是一個文學社團,社友們紛紛參與臺灣社會追求民主的各種抗爭。大一的社課是吳晟老師的兒子吳賢寧帶領的,他介紹兩位臺灣現代文學的標竿人物,一位是賴和,另一位是楊熾昌。賴和是臺灣新文學的先驅之一,他的詩與散文以白話文書寫,善用小說與雜文來揭露殖民暴力與階級壓迫,使文學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楊熾昌的筆名是水蔭萍,可以說是臺灣文學現代主義的濫觴。為了逃避日警的思想審查,水蔭萍選擇以「去政治化」的超現實主義作為創作姿態。他的創作帶著某種疏離的、外來者的凝視,仿彿以「異鄉人」之眼觀看自己的土地,語言與視角皆透露出殖民知識的痕跡。
從其琪的書寫中,往往能感受她身為「異鄉人」的身分,反而能養成一種精確地「看見他鄉」的能力;但是「異鄉人」的身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源頭,這似乎是上個世紀以來創傷文學的共同特色。文學作為一種見證、抵抗權力與療癒創傷的形式,這點不令人陌生。在納粹發動猶太人大屠殺所造成的歷史創傷之後,無數生還者在沉默與遺忘之間掙扎——有些人選擇噤聲,有些人則仿彿將那段歷史封存在無人可及的內在角落。比方說費修珊與勞德瑞所著《見證的危機》所提出的,是一種對這段「無法言說的過去」進行見證的另類敘事方式:透過破碎語言、或冗長而細緻的敘述,試圖召喚那些被壓抑、否認的經驗。這不僅是歷史的重現,更是一場為受難者發聲、為沉默創傷找到表達形式的倫理實踐。《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顯然也是一種見證。但和讀者較為熟悉的報導作品相較之下,這本冊子的文類顯然難以歸類定義。其琪一反過去向外凝視的非虛構書寫,反而採取了向內透視的日誌,以破除既有文字框架的體裁,將自身移動的經驗、夢境,乃至於內心那些脆弱受傷之處都昭揭於世。
即使書以「收集憂鬱」為名,其琪想說的話甚至比病症本身還多。她想要尋找比憂鬱還貼近自己的說法,也想為那些受苦找到更精準的歸因。書的一開始即提起社會學朋友提到的詞neoliberal subjectivity,用來給香港九龍城街上出現的大洞一個註解,同時能解釋自己如何「漂浮不定」,甚至「憂愁、焦慮、搖擺不定、認不清自己」。其琪似乎在為所謂的「創傷」尋找更適切的名字,我則對她提到的一種「例外狀態」印象特別深刻。在二〇二〇年三月那段期間她寫道「我過得忘了日期和星期幾,好像是故意的。我發覺自己在製造一種假象,把這段日子視為一個蟲洞或是什麼,而不讓它屬於原本的生命、時間。」移動本身就是一種生命的巨大斷裂,而當這個過程又突然被拋擲在疫情之中,時間、人、空間的種種錯置,人必須尋找一種活下去的方法。這個狀態不也像是人類學者Arnold Van Gennep在討論通過儀式時所提到的「閾限」(Liminality)概念嗎?在這個過度時空中,人仿彿失去所有的歸屬,從而思考一切事物的本質,重新發現自己能夠生存或甚至去愛的能力。
正如其琪所言「我用盡全力去把一日過得像三日一樣intense,見最多的人,看最多的海,聽最多的音樂,就好像每天都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天」這是用盡全力去擁抱並且對抗生命的冊子。在各種失落中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以及與萬物的關係。在那個閾限時空中,貓咪馬桶蓋是其琪最親密的家人,煮飯與書寫是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無論是養貓還是煮飯,讀者一定覺得作者實在「想太多」。在與親人相隔兩地時,其琪與貓建立了一種特殊的牽絆。這簡直像是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魔女宅急便》,魔女琪琪(Kiki,跟其琪綽號一樣那麼剛好)與她的黑貓吉吉(Jiji)之間的關係。他們之間不僅是主僕或寵物與主人,更像是內心與自我對話的化身。Kiki(無論是其琪或琪琪)與貓的對話,似是反映著她們對變動的世界所感受的不安。而煮飯亦是,無論是準備食材,或與人吃飯,都會讓作者想到身邊的人的處境。
讀這本書時,我不知為何常常想起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永遠的一天》的場景。年邁詩人亞歷山大,在生命的最後一天,回顧自己的人生與失落的愛情,並在偶然中遇見一位非法移民男孩。原本孤獨且準備迎接死亡的他,決定陪伴這名男孩展開一段短暫旅程,試圖在記憶與現實之間找回人性與詩的溫度。《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像是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一樣,不但色調相似,敘事的節奏也是穿插過去與現在,夢境與現實,藉由緩慢長鏡頭與詩意場景,思索死亡、記憶、語言與救贖的可能。這是一部關於時間、告別與存在意義的靜謐詩篇。當人們經歷痛苦,一方面或許需要為痛苦命名,但也需要讓這些痛苦本身有自己說話的空間。
最後,我想引用伊朗裔人類學家奧基德.布勞珊(Orkideh Behrouzan)的民族誌《百憂解日誌》(Prozak Diaries)裡頭的一段話:「有時,我們會採用那些能夠撫慰我們、並幫助我們理解經歷的語言(例如精神醫學的語言),這些語詞能減輕不確定與羞恥的重擔,而某些語調也最能投射我們的渴望。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語言、語調與沉默,會逐漸改變我們理解我們的故事、包括我們自己,以及這個世界如何持續運行方式。」這也正是我閱讀這本書時的態度,即使這本日誌大量揭露自身的憂愁,我看到的不是病症本身,卻是一個人如何包容、肯認自己的創傷,透過認真的感受、記錄,同時對抗又接受這一切。其琪透過養貓、煮飯與寫字來度過她的「例外狀態」;這三件事,都是奮力求生的行動。書末那句「我就是一邊哭一邊把飯吃完的人。所以我活下來了。」短短一行字,如此安靜祥和,又如雷般的震撼。
吳易澄|
精神科醫師,醫療人類學家,同時也是養貓人與慢跑者。目前任職於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與馬偕醫學大學。學生時期陸續在文學雜誌上發表詩作,曾著有散文集《詩所教我的事》。現在則專注在臨床工作、學術研究與教學任務中。
後記
2025年5月底,當我重讀過去5年的這些日記片段,發現自己讀到第16頁就已經全身發燙、心跳加速,坐在咖啡店伴著重金屬音樂流淚。我在書中多次提到「活下來」這件事,此刻我也真實的活下來了,但是說實話,我對於一個人如何在經歷許多痛苦後活下來,成為自己人生的倖存者,仍然是沒有頭緒。
「我終究活著回來了,什麼都沒殺死我。」這是2020年9月24日,我在結束14天的隔離之後,寫的句子。那時我因為回鄉過年和陪母親過生日,而在溫州遭遇 covid-19 的第一波侵襲,而有9個月無法回到臺灣。我想那之後的幾年,包括現在,我都仍處在一個漫長的復原期中,從那9個月,還有從2019年及後香港的動盪中復原。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覺得生什麼病都不奇怪了,因為吞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倖存是有代價的。
在這些日記中,直到2024年3月,我才發現那些非常接近死亡的時刻背後的意涵。那一天我寫:「我想,有時候我們想著去死,其實只是想逃。」往前一年的夏天,我去韓國訪問李滄東,他問我在《生命之詩》的結局裡看到什麼,女主角自殺了還是沒有呢?從我的回答裡,他輕易的發現了我對人生的筋疲力盡。2025年的現在,我更確信了面對這種筋疲力盡,我想要的是逃逸,是自由,而絕非死亡與痛苦。
2022年,我因為出版《流離之書》而去了各地做分享。那本書講的全是他人的生命,如果比喻成劇場,那本書的故事是我多年來寫作的「前景」(front stage),但敏銳的出版社編輯讀了我的自序後,很希望我能多寫一點劇場的「後臺」(back stage),也就是我藏在他人生命之後的東西。我拒絕了。三年後的這本書,此刻我在寫的,就是人生劇場的「後臺」,把外殼都剝掉,像蝦子一樣。
在那時的新書發表去到澎湖時,我剛剛重看了阿巴斯1999年的電影The Wind Will Carry Us。澎湖的風好大,我捨棄了書中的章節內容,轉而只講了島嶼和風。阿巴斯在電影中引用了伊朗女詩人 Forough Farrokhzad 的詩,”The Wind Will Carry Us”。 其中有幾句我特別喜歡:
My night so brief is filled with devastating anguish
Hark! Do you hear the whisper of the shadows?
This happiness feels foreign to me.
I am accustomed to despair.
Forough 在32歲死於車禍,比我年輕。我雖然無法知道她在1934年到1967年的時代,因為什麼而習慣和適應了絕望,但卻覺得深有同感。在奇士勞斯基的Bleu中,絕望等於藍色。我很喜歡藍色,但我不喜歡絕望,我只能像Forough一樣說,I am accustomed to this blue. 我幾乎快要習慣和適應了,這像硫酸銅一樣的憂鬱,像天空一樣的陰影,像宇宙漂浮粒子一樣的藍色。
在思考書名的時候,我問幫我寫推薦序的朋友Eason有何建議。他問我,我想傳遞的是關於死亡和憂鬱的事嗎?我回答,我覺得我想傳遞的是一個人如何在憂鬱中活下來的事,所以那個accustomed to就像是說「我適應了這種憂鬱」,我接受這個世界的動盪是常態了,我們必須適應它,我不是很完美的生活著,但我還是生存了。
感謝小小書房和小寫出版的沙貓貓,接受我任性的出版提議。感謝明知閱讀的會是痛苦,還是答應幫我寫推薦序的兩位朋友吳易澄和鍾耀華。感謝小貓咪馬桶蓋,今年是我們在一起的七周年,世上沒有什麼可以把我們分開。感謝寧緯,他是一個擁抱撐起的世界。
一個人不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氣才能出版自己的日記,真正需要勇氣的是,過去、此刻、未來的歲月中,我們決定寫下日記的每一刻。
熱愛重金屬音樂的咖啡店就開在臺灣文學基地隔壁,我去年駐村的時候常去。上禮拜,我走進店裡告訴老闆,我一年沒有來了。他笑著說,那這一年過得還好嗎?有什麼變化嗎?我說,我結婚了。他沒有像常人一樣說:「恭喜。」
他問我:「那有更了解自己了嗎?」
你呢?寫日記的你,更了解自己了嗎?
2025年5月31日 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