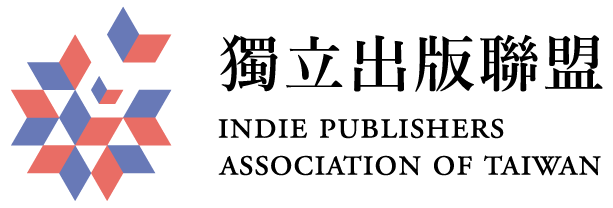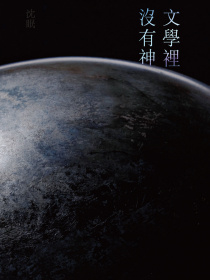失敗時候依舊擁抱高純度快樂──沈眠談現代詩得獎體
林夢媧/文.攝影
詩生活─詩人雜貨店主辦的純寫詩朋友會,每一堂課邀請一位詩人談一個主題,出版《文學裡沒有神》詩集、去年以寫給太太夢媧的情詩〈世界上最適合愛情的人〉獲時報文學獎新詩類首獎的沈眠,受店主陸穎魚之邀、擔任「純寫詩朋友會」講師,現身說法談現代詩得獎體。
▉大家都活得很中間,創作無須越過極限
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四年,沈眠參加大大小小各類文字徵獎、幾乎年產一百篇各類作品,「對於我這樣一個社交障礙的人來說,只想沉浸在寫作世界,文學獎競賽出乎意料非常適合我。一方面是對寫作能力的鍛鍊,而且有人免費幫我評斷作品的好壞。另一方面創作幾乎不可能維持生活,但文學獎救了我。一個獎金四萬元的詩獎,讓我意識到原來還有別的出路。」沈眠一吐情衷。
為何有得獎體?沈眠認為,就像波赫士常說的,所有文學類型定義的都不是作者本人,而是讀者。得獎體亦然如此,無非是由評審及主辦單位來定義,而不是詩人本身的定義。
沈眠爽利地說道:「當評審們的審美與創作觀,養出了一批具有同質性的作品時,也就是得獎體之生了。每一位評審都有自己的文學理念,聚在一起,只能妥協折衷彼此都可以接受的作品。這也牽涉到主辦單位對評審人選的抉擇,換言之,一切都是群體模式、多數公約制。但從評審紀錄也會看到某些輩分比較高、特別強勢、說服能力高的評審,如何左右、引導其他評審。」
對沈眠來說,得獎體也是中庸之道的體現。唯他也明言:「中庸不等於平庸。或者說,中庸是理解活著就無法逃離平庸的道理。實際上,大家都活得很中間──」他微一頓後復語:「人沒辦法太極端。太極端活著,不是瘋子就是怪物。可是人不是那樣活的,或者說不一定要採取這麼自損自傷的方法活著。不是一定要殺人剖屍才能寫殺人魔小說,我們有各種輔助工具,所以別把自己逼到超過可以承受的極限。」
▉文學是朝人性暗面持續地進擊
沈眠取用七首時報文學獎官網上刊載的首獎詩作進行解說。他強調:「透過單一文學獎作品,更能看得出得獎體模式。但首獎不代表一切。我的經驗反倒是有時是非首獎的詩作更能夠打動人。以首獎來談,主要是探討這些作品的精妙之處何在,當然也是假設各位是以首獎為目標。」
首先是得獎高手賴文誠寫的〈大夜班的護理紀錄〉(第四十三屆首獎詩),其太太跟女兒是醫療系統的人,所以清楚工作流程,詩裡充斥很多時刻與數字的記述,有一種客觀的精準感。沈眠表示,從前三行就可以看到特點在於醫療語言、詩歌語言的交互運用。且〈大夜班的護理紀錄〉充斥長行長句詩,塞好塞滿是得獎體的特徵。在主題上也有得獎正確性,寫得好不在話下,但也因為疫情的共通性經驗,讓這首詩更能夠脫穎而出,選擇醫護人員自然是大加分。
沈眠直言:「特殊的題材、職業或身分,在文學詩獎上也會佔便宜。為什麼文學獎很常見大量跟死亡、疾病與瘋魔有關的作品,因為文學本來就會朝異常、病態和變態等人性暗面持續地進擊。」
這首詩歌對醫療現場的冷異與緊張感,處理得頗為到位。尤其是Covid-19已經成為共同經驗,不管是傳染的恐怖、大封城、足不出戶的居家經驗,必須面對自己的孤獨,還有親人。這些疫情時期體驗很容易引起共鳴。
沈眠表示,將部分慣用詞語以詩歌意象替換,會讓原來習以為常的話語翻轉出新意來。「各位也可以試試看,用錄音機錄下平常在說話的聲音,一、兩分鐘好了,謄錄下來,應該會有幾百字吧,試著把某些詞語代換掉,就能快速生成詩。」他隨意指著旁邊的一本書,「比如將『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變為『一切孤獨都不會熄滅』,又或者是『一切孤獨都不會飛行』,這是詩歌很常見的替代、連結技巧。」
緊接著他分享陳盈慧的〈養動物〉(第四十二屆首獎詩),短句居多、偶爾配搭長句的風格,在文學獎裡本來就較不易得獎,畢竟同樣五十行的詩,每一行寫滿二、三十字的長句詩,資訊、知識、情感含有量就是遠大於一行僅五、六個字的短句詩。「不過,」沈眠話鋒一轉:「長詩不容易駕馭,往往會因為冗長、密集、囉嗦而讓人讀著讀著就注意力飄散。相反的,短詩比較能夠快速擊中閱讀者。〈養動物〉的短、長句調配得宜,有種很棒的閱讀節奏、體驗。」
沈眠講述:「誇張一點說,所有只讀詩就能寫出來的好詩,大概都被寫完了。如果能夠將別的領域化入詩歌裡,比如哲學、科學、物理學等知識,當然也會是對詩藝的某種激活。」
▉意象無非就是相遇,必須寫出意義
沈眠自言,張繼琳的詩作,是他很偏愛的,「不是陳柏伶《冰能》臺式諧音梗的好笑,也不是唐捐張牙舞爪狂亂縱橫穿梭古今的諷喻,而是一種中年大叔式的幽默,帶著心境、微微的牴觸感以及啟發性的幽默,而不帶有太大攻擊、傷害性。」
張繼琳〈舊石器時代〉(第三十六屆首獎詩),題名是人類剛懂得製造石器與以語言表達文學與藝術的最初時期,副標題為(我胡言亂語 讓舊石器時代又延續了數百萬年),此詩善用標題符號來做變化,特別是括號的運用,在每一段敘述之後都有一行括號、文字,作為前述的互補式詮釋。
「洛特雷阿蒙《馬爾多羅之歌》有一名詩句是『像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解剖臺上的偶然相遇』,亦即意象就是相遇,兩個毫無關係的事物被組合在一塊,從而誕生詩意。伊塔羅.卡爾維諾也談過大部分的意象都沒有意義,必須寫出有意義的意象。張繼琳的意象組構,打破文字的既定印象、規律,讓乍看平淡無奇的敘述句,都有了起飛感、驚奇性。」沈眠盡吐對〈舊石器時代〉的喜愛。
旋即他也提出告誡:「寫詩的人很容易著魔於意象的華麗技法,那就像是魔術,非常好玩。但整首詩如果充斥著意象,卻毫無意義,或者說意象太大、意義太小的話,讀起來很容易膩,只能給人一瞬的快感,過目即忘。」
凌性傑〈螢火蟲之夢〉(第二十六屆首獎詩)相較於前引的詩,是比較樸素的寫法,意象平實,自帶一種娓娓道盡情衷的誠摯,關於孤獨、慾望和自覺,是完成度極高的一首作品。
沈眠說:「瑞蒙.卡佛對才華、天賦有兩種定義,一個是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另一個是看見別人看見的、但看得更清晰、全面。如果代換來說,文學也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寫別人沒有寫過的,另一種是寫自己或別人已經寫過的,但寫得更深入和全景。比如隱匿從第一本詩集《自由肉體》到最新的《幸運的罪》,基本上就是環繞著貓、生病、書店、自然風景等等主題,但她一直往更深處挖掘。」
在沈眠而言,〈螢火蟲之夢〉也是相仿的狀態,不管是題材或寫法,都是已經存在過的了,不過凌性傑以最精準的詞語,容納了自身情感寄託,每一個意象都能切合與關聯,足以令人有共情。
▉創作者往往失敗於不符合社會標準
著有「流動三部曲」(《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Wonderland》和《愛的進化史》)的袁紹珊,是澳門詩人,沈眠多年前便注意到她的詩作,十分喜愛。而這一首〈快照亭〉(第三十九屆首獎詩)開宗明義一句「金屬疲勞的週五適合反抒情」儼然變為反抒情詩。唯沈眠也強調,整首詩還是充滿了各種情感宣洩、堆疊,可是用了一種硬派抒情的方法表達,同時更進軍女性在當代社會的複雜體驗,比如被「判定我是不合格的女人」,顯見袁紹珊的獨特視角。
「這樣一首充滿情感描述的反抒情詩,令我想到了蔡明亮的無敘事電影,或說是緩慢電影,比如《日子》,就是兩個人各自生活,最後聚在一起享受身體之歡,然後一起吃飯。隔著玻璃的長鏡頭,李康生要死不活地望著前方,落下眼淚,那一幕讓我瞧見了人的孤獨實相。蔡明亮的敘事充滿深情的凝視,所以沒有習慣的情節推演也無所謂。我們能夠完整理解一個人的孤獨,透過那幾分鐘的凝望。」沈眠感慨地說著。
旋即,沈眠進一步補充:「透過快照,把人像定格下來,去看見拍壞的人生。在〈快照亭〉的快速敘述裡面,隱含著慢速情感的表達,袁紹珊也把對自我的凝視,極其深刻地演繹出來。但詩人何止是不合格的女人,根本是不合格的人。任何類型、領域的創作者,不都是難以符合社會標準的失敗者嗎?而詩人唯一能夠產生自信的東西,不正是寫下一篇又一篇的詩歌嗎?那就是詩人的合格與價值。」
目前已移居臺灣的廖偉棠,其〈一個無名氏的愛與死之歌──對Bob Dylan的五次變奏〉(第二十二屆首獎詩)也是很標準的得獎體,「致敬詩在文學獎裡也較為容易取勝,當然必須慎選對象,如較為冷門抑或自己真心有所感的人。而不管是文學上的變奏或音樂上的取樣(OT),都要有本事讓致敬對象或取用的意象和片段,展露出新意。廖偉棠成功地將巴布.狄倫的歌之詩,帶入自己的情感與經驗,轉化出一首傑出的詩作。」沈眠平實地講述。
〈一個無名氏的愛與死之歌〉是長句長行詩,分為五節,每一節有三段,每一段有三行,結構明確,帶有規矩與制約,嚴整的寫法一如蜂巢,但每一格裡都躍動著蜜蜂飛行也如的節奏。沈眠直言:「長詩,尤其是長句長行,在文學獎的確是常勝之軍,但一百行的詩作,要一氣呵成寫就,很考驗詩人的功夫,同時也是測試評審的耐性。適當的分段結構,無疑是寫長詩最好的節奏校正器,讓人閱讀時能夠有良好的呼吸感,不會窒礙難讀。」
▉寫情詩之必要,文學最關注失敗而不是成功
沈眠詩作〈世界上最適合愛情的人〉是長達近一百行、分為四大節的情詩,乃是獻給太太林夢媧的作品。他表情微妙地說:「時報文學獎是現場公布名次的機制,老實說,我最初以為頂多只是拿佳作,畢竟情詩並不符合現代潮流。當國家、社會、疫情和戰爭議題如此巨大之時,我們都活在資訊焦慮、生存壓力裡,好像有更多必須思考、表達的事情,寫情詩就變得一點都沒有那麼重要。」
愛情似乎在當代正在失去活力,或者說,正在變形,不再有永遠,也無須是忠貞。簡單來說,沈眠認為人們好像進入一個不再信仰愛情的年代。然而,與太太之間的情感是沈眠生命中最重大的存有,每年都會寫情詩給她,以文字述說愛即為信仰與命運的真實所感。沈眠是這般以為的,如果愛情在現實婚姻、生活磨難中仍舊是不死的,那麼情詩就是不死的。
沈眠分享自身想法:「如果只考慮獲獎機率,一開始就不該以情詩比賽。從這幾年情詩在文學獎的缺席,也不難看出此種趨勢。這首詩能夠拿首獎,是幸運的成分居多。當別人都在寫比較符合主流的作品時,有一些與潮流相反的東西,反而會出線。」
至於如何面對未得獎或詩寫不好的挫敗感?沈眠的視線底夾帶著坦然:「對成功的渴望與需求,是整個時代製造出來的風氣。可是究竟要什麼樣才算是成功呢?沒有得獎就表示詩寫壞了?我不這麼認為,把一個創作好好完成的滿足感是內在體驗,不是外部評價可以取消的。換句話說,寫完一首完整的、與自己心靈同步的詩作本身,我就認為是成功。」
沈眠真誠地述說:「得獎體是現實存在的,但同時也是虛無的,因為它終究是一個評量出來的東西,某個部分來說就是一個數字,第一名或第二、三名,還是落選,並不能全然地代表好壞,更不可能抹消創作的心情與意義。文學是有感的,人生被轉化成有意義的文字,跟生命、此時此刻的生活緊密相關,這一點才是創作者的心魂之所在。」
他自承即便到現在還是會寫出爛東西,還是常常覺得自己並不夠好,或者說常常有一種必須從頭開始的感覺,「每一次寫一首新的作品,就是一次重啟。寫作是快樂的,也是意義非凡的。雖然過程裡身心充滿痛苦,結束了也要煩憂發表的機會與場所。唯寫作本質上就是無與倫比的快樂,我是一個失敗時依舊擁有高純度快樂的人,這樣的認知,或許就足夠我們在慘澹的現實裡支撐下去。」沈眠語音鏗鏘地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