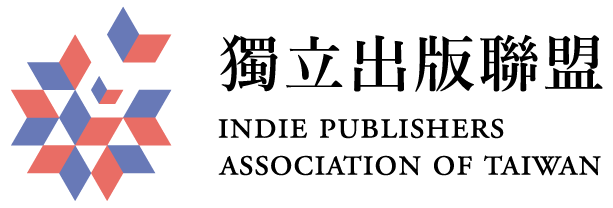日子靜緩豐盛。
不遠的將來,我們見面,
像家人那樣擁抱。
寫下眼中萬物、愛與誠、症候與跡象,寄出給你。盼回。
移動、居無定所,是我永遠的家。
貪什麼呢?貪一無所有,從頭來過。
心有所愛,就把自己留在那裡。
最遠的最近,流動於歐、亞、美洲的詞彙與心意
年餘的文字往返,恆久緊繫的熱戀
世界人的直擊、旁觀、念想與回憶
建立新視野,思量存在的依據
我喜歡移動,定居在一個地方,彷彿不是我的宿命。也許是從小就時常搬家的緣故,我對環境似乎有著過人的適應力。前半生在台北遷徙,後來則是遊走於台德兩地。移動中,我總是會攜帶各種讓自己安心的物件。行李箱裡面有輕便的慣用物品,每到一地,我攤開行李,那種熟悉感就會伴著我度過時時刻刻。 ──彤雅立
超過負荷,就把自己變得更能負荷。所有意外於是成了禮物。雅立,你還記得我們六月的時候沿著特格爾湖漫步嗎?現在,湖面結冰了。像你當時晶亮的眼神。聊起病變的細胞和心念讓我們意外轉向,渴望靜緩,渴望在移動中停留,告別我們的過度用力。超過負荷的意外,真的成了禮物。──吳俞萱
熱戀∣政治與地理上,邊境指鄰近國界的區域,用於緩衝、加諸限制,也可完全開放。它是地圖上是清晰的線,實則引伸為不同型態的曖昧詞,形容於國族歷史、家族血緣、宗就與生命觀的藩籬,小至人與人的芥蒂。俞萱與雅立,半生往返異鄉與故鄉之間,無論方向,每一決定都為彼此帶來身心震盪。如今世界充滿有形與無形之界線,思考那道隱形線段前,是否更該理解人的共有性?「我在意的不再是自己的完整表達,而是我跟所有人的完整連接。」命運是緊密織就的網,走上其敘事脈絡,神祕且寬闊。本書是交叉懸垂的兩部個人史,從旅途初端的飛行談起,正視故鄉、病與藥、價值觀調和、旅途中的旅途、族群難題……是過客,亦留下身影,以信件交換試探生命的新意與反芻,將自身對世界的熱切交予對方。一場無邊界的愛,陌生國度是生命延伸,而學會與每一種相遇共處之後,所謂邊境已然為何種詞性?
更多討論,歡迎收聽「南方家園小客廳」open.firstory.me/user/ckih360qw5fii0826otr104sx/platforms
本書特色
★旅行散文創作的全新光點
★一年餘的往復書簡,來自歐亞美三大洲的思索與提問,兩位作家的關係建立與國際觀之回望與重設。
★從真實的邊境現況,探究存在定義、價值觀調和、族群難題、社會局勢等等異地故鄉之日常,生命觀的重新打磨。
作者簡介
吳俞萱
台東人。作家、譯者、研究者。目前就讀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
渴望把陌生的異境走成家。著有《交換愛人的肋骨》、《帶著故鄉行走》等書。
彤雅立
台北人。作家、譯者、研究者。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電影學博士。德語文學譯作二十餘種,著有《邊地微光》、《月照無眠》等書。
目錄
往返之一
把異鄉走成故鄉__美國佛羅里達(2023_2_5_SUN_13:30)
遙遠的抵達__台灣台北,2023_2_20_MON_19:00)
往返之二
覆蓋__美國紐約(2023_3_6_MON_07:12)
晨霧藥方__台灣台北(2023_3_20_MON_13:30)
往返之三
總有一種時差__法國庇里牛斯山(2023_4_7_FRI_05:12)
每天離自己近一些__台灣台北(2023_4_20_THU_21:00)
往返之四
洗__法國努瓦耶(2023_5_6_SAT_06:15)
讓生命留下餘裕__台灣台北(2023_5_21_SUN_23:00)
往返之五
減少分心的生活__德國柏林(2023_6_7_WED_07:59)
更好的生活__德國魯爾(2023_6_20_TUE_22:30)
往返之六
以遠方為家__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7_6_THU_16:08)
語言也是一種土壤__德國魯爾(2023_7_21_FRI_12:30)
往返之七
我們將要共享同一座身體__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8_6_SUN_16:16)
移動的日子__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8_6_SUN_16:16)
往返之八
愛__土耳其伊斯坦堡(2023_9_8_FRI_08:12)
踏實__台灣台北(2023_9_26_TUE_11:20)
往返之九
生活已在發生__瑞士蘇黎世(2023_10_10_TUE_08:05)
靜默的平和__台灣台北(2023_10_18_WED_22:31)
往返之十
情願__德國柏林(2023_11_6_MON_11:15)
邊緣的人,擁有穿越的自由__德西小城(2023_11_22_WED_18:30)
往返之十一
一千年前__德國柏林(2023_12_6_WED_04:26)
孩子__德國柏林(2023_12_21_THU_23:51)
往返之十二
苦澀和甜蜜__蒙特內哥羅(2024_1_8_MON_08:18)
際遇與緣分__德西小城(2023_1_23_TUE_15:00)
後記
世界人
走,過去就是邊境
後記
世界人
吳俞萱
結束通信之後,我和雅立在台東見了一面。我光光的頭,冒出新芽。雅立衣服上的一顆釦子掉了,她不慌不忙打開隨身的背包,取出剪刀和針線,俐落縫補起來。
世界人就是,把空缺也當成行囊,輕輕揹著。
從二零二四年初來到年底,我頭上的毛已經落到肩膀。春天去了一趟義大利,待在塔可夫斯基拍攝《鄉愁》的村莊。入夜起霧,我重看《鄉愁》,竟然感到運鏡和剪接的緊迫。原來,年輕時看到的緩,突顯了缺乏鄉愁的鳴和。現在接收到的緊迫是全然懂了那回望的吞噬力。
一推開窗,一陣雨聲,一點現實的空隙,隨便都是回憶滲透的入口。也根本不用回望,過去是刀,沒心沒肺地直直殺來。所謂的平衡,有時只是不動聲色,任刀刮幾下,現實就越來越平滑。去到《鄉愁》終局的那座修道院,我跳了一支舞,送給塔可夫斯基。
別再問一個人失去什麼,要問的是:我們曾經一起創造了什麼?
謝謝子華、達瑞陪伴我和雅立創造我們的鄉愁。沉入當下的深度決定了熱戀的品質。當下需要被警覺,才能被體驗。謝謝雅立的溫煦和堅定,引我細細凝視流動的每一個當下。不曾有過的東西無法被喚醒。如果她看向我的目光與所有人的都不一樣,那是因為我對她付出了我不曾給過其他人的東西。
走,過去就是邊境
彤雅立
在社群媒體尚不發達的時候,我曾經開了一個部落格,名字叫做「走,過去就是邊境了」。邊境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浪漫的字眼。它是各種文化與認同的邊界,充滿了異質性,涵納了各種自我與排拒,並且眼見衝突的降臨。那時候,我先後在女書店與《破週報》工作,這兩個地方也有著強烈的邊境性格,而且不屈不撓。在那段期間,我時常帶著筆記本在身上,腦海中總是有字句傾瀉而出,我得把它們記下來。留學柏林的時候,我剛滿三十,對於寫作,其實並未抱持多大的夢想。我並非早慧之人,也沒有當藝術家的決心;也許那份自我排除,是源自於成長的經驗。臺灣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兼具的地方,解嚴過後的社會環境,既有傳統也有前衛。其中的優缺點,無不影響著我,使我成為現在的自己。
我在柏林西郊的學生宿舍,開始整理自己的詩作,發現自己的作品累積到兩部詩集的量,於是與當時也留學柏林的美編,在她位於東郊的宿舍裡,一同為《邊地微光》進行編輯與排版。也許靜靜發表作品,終究會覓得知音。第二本詩集出版之後,我與俞萱通過幾次信,並且就此,我成為她部落格「你笑得毀滅像海」的讀者。她的筆鋒熱情、溫柔且銳利,對我來說,她是真正的藝術家──到日本學習舞踏,創辦影詩沙龍,拆解邊境、走向無地。那幾年,幾乎想要隱身的我,默默地閱讀她,無形中也汲取了一些力量。
是的,力量。這個世界充滿各種力量。當我們被現實生活擊垮,軟弱依舊會生出力量。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務實地生活,不願意面對有關創作的一切。我沉浸在翻譯與研究的世界裡,刻意地與書寫保持距離。原因無他,正是因為我害怕被注視,以及書寫帶來的情緒滿溢。翻譯與研究,則多了幾分理性,能使我的心緒更加安穩。這次與俞萱重遇,並且對寫我們的世界與心靈,因著我們的靈魂相似又像異,我重新認識了自己,也從書寫當中更加直面自己的人生使命。我知道我是我自己,無論我是否正在寫作、翻譯或研究。我知道我不需要任何的定義。這是俞萱教會我的。
第二次移居德國,此時的我已步入中年。我在德國西部,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現在的我,能夠更安靜地寫作、翻譯與研究,並且對於時間的流逝毋需過度在意。還記得在柏林的歲月,為了謀生存,我鎮日在圖書館中,白天寫論文、晚上做翻譯。我將亞洲式的過勞生活移植到柏林,幸好這座城市作為首都,忙碌的人生活其中,毫無違和之感。如今在萊茵河的腹地上,氤氳的空氣、悠閒的氣息,搭著地鐵看著河谷上的人們漫遊流轉,漸漸地我也沾染了一些緩慢的氣息。
上星期,我看了一部電影,叫做《明特與康丁斯基》,是由藝術家康丁斯基的真實故事所改編。這部電影使我想了很多。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紀末,康丁斯基三十歲,放棄俄國法律與經濟學的教職,移居德國開始繪畫創作,直到流亡巴黎之前,度過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階段。在「藍騎士」畫派與「包浩斯」藝術學校之外,當然也有著深刻的感情生活。尤其與藝術家明特之間的故事,在大時代的顯映下,更增添了傳奇的色彩。電影並非全知視角,而是站在女主人公的觀點看事情。偏偏論及感情,總是剪不斷、理還亂,每個人總有他的視角。為了瞭解這段人生的面貌,我去看了康丁斯基的作品,也買了一本他後來妻子的回憶錄。兩個藝術家在一起生活,是一件困難的事;電影中的兩人,都將畢生貢獻給創作,並且留下大量的作品。我時常好奇,在步入包浩斯時代之前的康丁斯基,究竟是如何與明特一起在鄉間小屋過著尚無電器的生活,甚至能夠好好創作?創作油畫是很花時間的。我看著明特與康丁斯基的作品,心想,也許他們的屋子裡面,確實有著各自冥想與創作的空間。那種自我的存在與孤寂,才能夠造就藝術品的誕生。
我想寫作也是這樣的。它是一種獨自的狀態。當我不再需要追逐時間之後,我才有機會開始真正地書寫。我的詩歌創作,源自於生活的吉光片羽,在很短的時間可以完成。靈感總是捉摸不定,來了又走。寫書則是另一種狀態。它需要沉澱、思考、醞釀與構思,好比畫一幅大型畫作。
在我已經不再拘泥於自己的定位時,與俞萱的通信,漸漸地把我引回了創作的路途上。我是誰?我想也許已經不再重要。我卻要引用尼采式的說法──我要,我去做。不知道俞萱一家人的生活走到了地球的哪裡?上次在臺東見面時,她開心地說著成立「走向刀鋒」的事。這樣銳利的名字頗有俞萱的性格,彷彿是她部落格的延續,而從事的則更面向公眾。在紛亂的時局裡,人心似乎更加徬徨無助。我們是誰,要往哪裡去?無論是否有過戰亂,我所經過的人們,一張張的臉龐,大多寫著寂寞。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韓國告訴大家:時局如此,不宜慶祝。那些走過邊境的人,來到德國,面臨的是身為新移民的挑戰,一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移民。在這裡,我還在建立新的生活,我會每星期去森林裡散步一回,照顧好自己,蓄積能量、致力創作,同時兼顧謀生的事。我知道我正慢慢長成一棵樹,就像所有的人一樣,成長並且老去,在盛年的時候,它開枝散葉,可以將生命中所吸納的養分,透過各種方式給予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