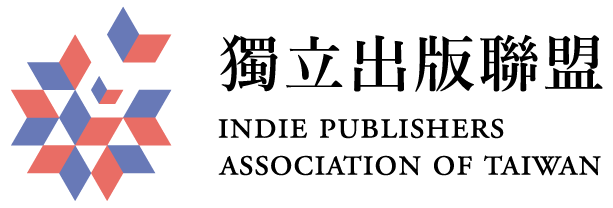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國鎮》續篇,「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野夫又一鉅作
──作家野夫直探中國文革後半世紀以來民族、人性之殤的究極之問!
這是野夫孤獨的棋道,以小說的綺麗幻異之術,完成做為民間反抗者的收屍人之志業。
一本政治與愛情、性和死亡、革命及信仰交纏揉合的絕倫之作
兩個陌生的男女,在武漢新冠病毒封城的前三天,相約來到泰國的某個孤島避居七日。他們在一起探討愛慾、生死以及信仰這些人類永遠的困惑,在最後的時光所揭示的卻是中國半個世紀來,民間志士所奉獻和犧牲的巨大秘辛……本書可以視為是作者前一部小說《國鎮》的續篇。兩個人的孤島,一個家族的命運,濃縮了中國當代史眾多的大事紀。無論語言、結構、故事、人物塑造和思考深度,都足以讓讀者難以釋懷。
──愛情不是誰傷害了誰的問題,而是我們都被這個時代謀害了。
──而他和她的這一次旅行,真可能是生命中最後的盛宴了。
──這個政黨和體制,本身才是最大也最邪惡的病毒。
──他一直逆行於此荒誕年代,一直九死一生地救贖著自己。
──我們這一代,一定要給孩子留下一個再沒有恐怖的國家。
「華族的記憶,太多的秘辛被曲意塗改為『盛世』的華章。我在我的成長裡窺見,無數家族的血腥往往都散如青煙,更不要說一個國家的編年史,竟然充斥著無數隱瞞抹殺。一望無盡的反抗者,他們不僅肉身死於刀兵;更加可悲的是他們曾經的勇毅精神,還將身影俱無地再次被扼殺於史紀。我常在酒肆茶舍邂逅的平民口中,知悉更多折骨裂肉的往事。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無辜;竹帛難罄的悲劇,就這樣荒蕪在黃土壟上。」——野夫
本書特色
•野夫直探中國文革後半世紀以來民族、人性之殤的究極之書,紀錄恐怖統治下的反叛者群像、歷史與精神,劍指天安門六四事件遇難亡靈名單、新冠病毒深不可觸的黑幕,悍勇無畏地呈現中共政體不啻天字第一毒的病邪本質。一本政治與愛情、性和死亡、革命及信仰交纏揉合的絕倫之作。
•《國鎮》續篇,歷時四年創作。描寫上個世紀七○、八○年代到2030年,文革後半個世紀的中國。
既是小說,也是紀實記錄。記錄整個國家的一場「病毒」時代,也是中國民間的反抗歷史。
作者簡介
野夫
男,土家族。1962年出生於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縣最邊遠的小村。1978年考進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同年開始詩歌創作。1982年組建鄂西第一個詩歌社團「剝棗詩社」。1985年擔任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常務理事。1986年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湖北省「後現代詩人沙龍」,出版詩集《狼之夜哭》。1988年分配到某省會公安局,1989年因為支持學生,公開宣布退出警界。之後因參與掩護民運人員及「洩露國家機密」,被捕判刑。1995年減刑出獄,到北京謀生成為民營書商和自由撰稿人。
自80年代開始創作以來,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約三百多萬字。曾獲2009年「當代漢語貢獻獎」、2010年《江上的母親》一書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2011年「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2012年「中國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2012年應荷蘭國家文學基金會邀請成為阿姆斯特丹駐市作家;2013年受邀至德國科隆擔任駐市作家。2014年開始,與余英時同時被宣佈被禁止在中國出版發表文章和書籍。 連續五年獲得海外網媒評為「全球華人年度百名公共知識份子」之一。
在臺灣的出版品為:《江上的母親》、《看不見的江湖》、《門後的守望者》、《1980年代的愛情》、《大地呻吟》、《活著為了見證》,以及長篇小說《國鎮》。
目錄
代 序 島與島的對話 楊渡&野夫
尾 聲 末日審判(2030年……)
第一天 如約而往(2020年1月20日)
第二天 永恆愛慾(2020年1月21日)
第三天 生死密鑰(2020年1月22日)
第四天 迷途執念(2020年1月23日)
第五天 隱祕生長(2020年1月24日)
第六天 永劫不復(2020年1月25日)
第七天 致命託付(2020年1月26日)
後 記 絕望中的反抗 野夫
後 跋 東方大陸深處悲愴的吟唱 (法)沃.熱拉.塔瑪
代序
島與島的對話:楊渡×野夫
楊渡:當年你在德國開筆寫《國鎮》,疫情中在清邁開筆寫《孤島》,最終在臺北完成這一長篇,真是很有意思。我想你會不會是在離開故國家園之後,隔著遙遠時空距離去看它,會有一種更清晰的感覺?
野夫:這就像是宿命一樣,我自己還沒有意識到。《國鎮》我是通過一個小鎮寫中國的文革史。而2019年底新冠病毒開始,我在泰國一個島上,決定要記錄祖國即將發生的這場影響人類的浩劫。
楊渡:你當時就知道這段時間裡面所發生的災難,必將成為未來的歷史?
野夫:當時我就意識到這場疫情,一定不僅影響中國的國運,必將影響人類世界。但沒想到會持續那麼久,死去那麼多的人。我有心想要即時性記錄,所以說這既是小說,同時又包含許多非虛構的現實。我其實只寫了武漢封城前後這七天,但通過人物的回憶,記錄了整個國家半個多世紀的民間反抗。或者說這一場疫情不只是醫學、生物學的事件,而是這個國家一直處於一個病毒時代。
楊渡:在2019年十二月的時候,我們還曾在上海小聚,當時你告訴我可能到清邁去。我後來就在想,你是否有一種本能的直覺,讓你預感到要開始發生什麼事情呢?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訊息?
野夫:很多朋友能夠證實這一點,更早之時,我就跟很多朋友表達過我的這種憂患,我覺得國家正在走向一個危險的階段。當時我不敢斷言是一個大的病毒,但我就是有種預感,這像是詩人的直覺,不是神秘的玄學。我覺得有一場大難即將開始,我給一些師友提出警告,說接下來的時代可能要面臨深淵。但我沒想到一走就走到了今天。作家有這種直覺,並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奧威爾(臺譯:喬治.歐威爾)寫《一九八四》的時候,來自於直覺。徐志摩對蘇聯的警覺,其實超過了當時很多政客和學者。
楊渡:你此前通過家族史來呈現整個國族的大歷史,你現在的《孤島》,同樣是兩個人彼此打開的回憶,從中見證這半個世紀的中國痛史。你說「一個國家的編年大事紀,竟然充斥著虛構與抹煞。必須借由對過往親友的命運檢索,才可能更多地窺見中國人曾經走過的歲月本相。」我覺得這是《孤島》裡特別動人的地方,用家史去印證國史,彷彿就是你整個寫作的總脈絡。
野夫:我最初的寫作都是非虛構,你要想深知一個真正的1949年之後的中國,不能從宏大的政治敘事裡去瞭解。我正好處在這個時代,窺見了1949以來的中國實相,我不把它記錄下來,會覺得愧對歷史。《孤島》應該說是《國鎮》的續篇,《國鎮》出走的那兩個人物,在文革倖存下來的他們一家,在未來參與到反抗專政的各種重大事件中。我一直寫到了2030年,預言到六年後了。看似虛構的故事,實際上真實地記錄了中國從七○年代開始的那一代思想者,直到我輩以及更年輕一輩的反抗。一代一代的覺醒,它是有一個內在脈絡的,並非突然冒出來的人物。我一直堅信不疑,在中國民間這一脈反抗的骨血一直存在。我通過一個家庭四個人的命運,把半個世紀中國人悲壯的抗爭,濃縮在這樣一個孤島七日裡。
楊渡:比如說當時《青年論壇》對1980年代的啟蒙,你把它放到這個家族的脈絡裡,你試圖去呈現的是一個在中國整個大歷史裡面,一直存在著這樣一個文化思想的民間傳承?
野夫:對,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使命,就是來世界見證和記錄這一切的,我通過這個小說把它寫出來,可能會讓更多的人去研究那些被埋葬的歷史。我們沒有能力成立組織去發動革命,但你記錄的使命是天賦的,不能始終回避這些話題。我這書中隨便一段史實拿出來,都可能是一個巨大的題材,我把它掀開之後,無數有興趣的人可以把每一個話題研究得很深很深。
楊渡: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在過去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的,沒有人去把這樣的一個脈絡連接起來?就像1969年到1989年之間,那個時代裡的思想啟蒙,對整個後來時代心靈史的影響,其實有一脈相承。即使是在海外的寫作者,好像也沒人像你這樣把整個脈絡整理記錄下來。
野夫:大陸的多數寫作者要依附於體制,而這些都是被稱之為禁區的東西。這些禁區就像臺灣在戒嚴時代,也會有很多禁區是不能去碰的。我們整個黨國一直處在高度戒備之中,但凡還要依附吃飯,還要想安度晚年的寫作者,他會自覺地不去碰觸這些敏感區,會自覺地屏蔽這些歷史。海外流亡的那些同道們,他們是熟知這些歷史的,他們甚至就是這些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很多資料都在國內,當初沒有帶走;而流亡的困窘艱迫,很難有一個舒適的條件來慢慢記錄。可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使得人們就放下了它。就像我這裡面談到的黃雀行動,多少人是被這個行動救出去的。按說他們應該詳細地記錄這個過程,個體的回憶有,但是沒有作為一個大歷史畫卷來描述。
楊渡:你在《國鎮》裡面寫到的吳群恩這個人物,在文革中他是起來造反的學生;但在《孤島》中1989學生運動起來時,他卻採取了一個更審慎去思考、去行動的方式,然後提出他的對策。可他彷彿對那個時代也毫無辦法。這是不是那個時代,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共同心靈和憂患?
野夫:這個角色是《國鎮》裡走出來的一個高中生。真實生活中,類似於楊小凱、遇羅克、王康這一輩人物。他們在那個年代的思考已經很深了,在地下設計中國未來的道路。這些人在文革中多數參加了造反派,被血腥打壓甚至被處死。由於吸取了文革的教訓,當他們走到了八○年代末期,學生運動又開始爆發的時候,他們真的要比我們冷靜理性。我通過吳群恩刻畫了這樣一個有極深思考的人,而且又是那麼堅定的真正反抗者。但是他認為反抗不能盲目激情,不要輕易去犧牲一代人,做一件幹不成的事情。因此他在這場運動之初,表現出那樣的冷靜理性和反對。他的可貴在於――我雖然反對你們這樣,但是如果你們失敗了,我一定來為你們收屍,哪怕為此坐牢。同樣,水姑娘在《國鎮》裡是一個柔弱的小家碧玉,她這樣一個忍辱負重的女人,最後也成為這個惡世最勇敢的母親。其實在今天的中國,走在最前線的許多都是女性,我要借此向這些偉大女性致敬!
楊渡:那麼,你怎麼看待一個家族歷史中,人的典型性跟這個時代的連接?
野夫:國運即家運,我們每個人活得如此不堪,都與我們這個時代非常相關。個人悲劇是這個時代巨大悲劇的分支,我宿命地投錯了胎,就必須要承受這個時代的一切。唯一我給自己的使命就是我可以承受,但我要把它記錄。我虛構的只是人物,背後的歷史全部是真實的,是完全血腥殘酷的歷史。《孤島》稿本我只給了很少幾個朋友看,幾乎無人不哭。我們在哭這個時代,也在哭我們自己,哭書中人物那麼慘烈的命運。
楊渡:在你的書裡面我還看到一種民間的人情義理。那麼多的運動迫害,很多知識分子都被打服了。可是在文革之後,怎麼從這樣的荊棘裡面,重新凸顯出一批反抗的脊梁?這個反抗的脈絡是怎麼被傳承下來的?
野夫: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歷朝歷代都有反骨,這種反賊現象是不絕如縷的,這就是所謂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譬如我出身於共產黨基層幹部之家,父母並不會給我反叛教育。那我身上的反骨從何而來?其實就來自於我生活的「國鎮」,鎮上那些江湖人士和民間反叛者,給了我最初的薰陶。我少年認識的部分武漢知識青年,對中共新政十七年充滿了仇恨和批判。每一個鄉鎮都有這樣一些人,稟賦和家世很好,卻一直被打壓。這些大哥大姐總會有隻言片語告訴我,這是一個不好的時代。我們土家族是巴人後裔,古稱五溪蠻,在1970年代還有農民暴動。那其實只是一些為了基本生存權利,而真正在拋頭顱搏命的人。
楊渡:很好奇中國這些知識分子,即使在那麼艱難的時候,不是在思考個人的出路,而在思考這個國家民族之出路,好像有一個文化內在的基因,是有一個大的使命感?
野夫:中國傳統文化裡面,不管儒家、墨家,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思想一直存在,這種思想是在人格和理想上的影響和薰陶。我認識的人就有許多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想要為天地存心,為生民立命,這都是知識分子應有的使命感。中國歷代不缺這樣的人,可能他一生自己過得狼狽不堪,但是卻心懷天下,所謂的要為蒼生說話。我認為當年臺灣也一樣不乏這種骨血。
楊渡:你對於政權有一種批判和失望,但是你對於民間社會,好像還存在著一個恆常的信念,彷彿人在最絕望的時候最終承載他的只是在民間。
野夫:對,這也是我一直想要用文字來表彰的。因為任何一個王朝最終都會覆滅,否則我們現在就還是秦朝。即使王權的法統和帝王的血統都變了,但是民間的道統還在。
楊渡:這麼好的《孤島》,你為什麼會猶豫它的出版?
野夫:我算是平生膽大的人,在這個時代都感到有所恐懼,我認為出版之後,有可能給我帶來災難性的打擊。最後為什麼還是決定要出版?是因為我記錄了幾代人的反抗,那麼多偉大的事蹟,背後那麼多真名實姓的人物,既然寫了我就要把它公開,我也應該成為反抗隊伍中的一員。我要自己都不敢加入這樣一個陣容的話,我會在九泉之下愧對我記錄的那些人物。你們無法想像一本書有可能給我們帶來的打壓、管控、限制,甚至更嚴重的事情都有。遇羅克當年寫一篇文章就被槍斃了,我們今天距離遇羅克的時代未必有多大的距離。
楊渡:我在你的書中還是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就像白紙運動,它彷彿是一個時代大家共同覺醒之後,用無聲無言代表了反抗。你怎麼看待這樣的一場運動呢?
野夫:這也是一種革命的方式,時代科技在進步,社會革命也在升級。傳統的革命方式不僅沒有可能,坦率的說還不一定值得提倡。白紙運動是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沒有領袖,沒有組織,甚至沒有預謀,這才是一代人的覺醒。現在年輕人的這樣一種方式,在未來有可能給這個民族帶來一個不那麼血腥的改變。華族已經有成功的樣本,就是你們臺灣,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就讓這幾千萬人獲得了憲政法治自由民主,這就是希望所在。
楊渡:你在《孤島》裡面寫到了2030年,男主人公面對著一個廣場,期待愛人的到來。我看到那個場面非常感動,因為那是他面對一個新的時代,他不止是在召喚故人,而且是在召喚一個未來,一個人面對一個空蕩蕩的異鄉,去召喚他的故國的未來。你為什麼會在這個故事裡,想要用那麼美好的愛情故事當一個軸線?靈與肉互相接近的過程,是一個互相發現身體內在許多未曾知道的祕史,互相慢慢揭開國家血史的殘酷過程。你彷彿是故意在做這樣一個很細膩的安排。
野夫:我開始寫的時候就想好了,雖然這個書有史學價值,但它畢竟不是史學著作。如果未來的史學家們要寫1949年之後的中國反抗史,他們也會寫出我提到的那些內容。但我是借用文學的方式來反映歷史,文學需要有可讀性,有懸念,有情感衝突,我需要把大歷史放進具體的個人命運中去寫。愛情當然是人類永恆的主題,我也希望這個書首先要讓人願意讀下去,於是我表面上在寫一個愛情故事,背後則是驚心動魄的偉大歷史。愛情只是一個殼,我這個可能叫借殼上市。
楊渡:那個殼也蠻好看的,太迷人了。我覺得能夠把愛情與慾望,很細膩地一邊剝開肉體的局限,同時也撥開彼此的心靈,很像剝洋蔥一樣讓人淚流滿面,我覺得那是非常動人的一條線。
野夫:我這個小說與政治密切相關,但如果僅僅變成傳達你的一個政治概念、政治理想、政治鬥爭的東西,那就不是文學,或者說那不是一個成功的文學。我希望人物塑造成功,讓人過目不忘。哪怕如此與政治相關的這個小說,我還是要讓每一天的生活絕不重複,每一個階段的語言都有它的味道。一男一女在一個小島上,一個孤絕的環境裡待七天七夜,這是考手藝的一個寫法。我花了四年半才寫完這十幾萬字,這個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有趣的嘗試。
楊渡:這個技術我真的很困難,嘿嘿。我們都知道一個寫作者離開家園,他寫作起來當然有種歷史距離感,可以有一個更遠的全域性的關照。你在寫這種人物情感的貼切性上面,會覺得有距離感嗎?
野夫:我恰好就是把這個故事放在泰國的,我又生活在那裡,那一切背景都是真實的,民風民俗,甚至他們點的菜單全部都是真實的。至於談到的中國歷史,那就完全是我爛熟於胸的故事,是我記憶的史冊裡面打開就有的東西,剩下的只是我怎麼把它放在泰國的孤島上面,一頁一頁地整理出來。為了讓這個小說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寓言,我不僅把它變成了一個愛情小說,同時我還把它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討論。他們討論的是愛與情慾,生與死,信仰與救贖,這是人類永恆的困惑與主題。我不僅講歷史,講反抗,也不僅是講情色,還把這些思考全部植入進去,能夠給人更多的啟發和回味,讓它更厚重一點。而我在寫作的過程中,自己甚至也經歷了愛與生死的考驗,經歷了信仰的掙扎,還是很嘔心瀝血,自己寫著寫著哭了好多場。因為它既是我記憶中的東西,也是我生命中的體驗,我也為自己記錄和創造的這些人物而感動。
楊渡:你寫完最後一場的尾聲是在臺灣,自己一個人在淡水的住處大哭一場,之後再出來跟我們聚餐喝酒,朋友之間只能這樣互相安慰慶幸。我作為一個讀者,深深為這個世界能夠產生這樣一部作品而感到幸運,也希望我們的讀者能夠分享。在這裡坦白說,我個人所看到的不只是反抗史,而是近半世紀以來中國內在的心靈史。
野夫:我覺得一切都像是天意,2020年初疫情正在大爆發的時候,我在泰國的一個小島上開始寫作第一段。然後四年半後,我依舊沒有回去,又來到了臺灣這個大島上,完成了它的尾聲。一切都是在島上,這就像是某種命定。這些島就像一個巨大的隱喻,而我們自己,很多時候也彷彿活成了自己的孤島,在汪洋中砥柱一般繼續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