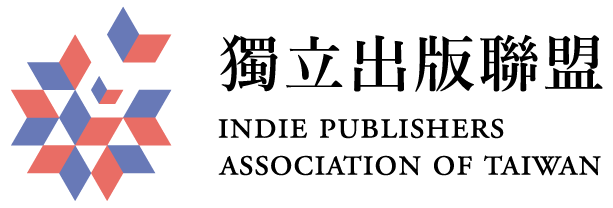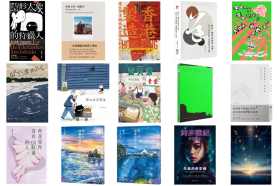凋零與豐收:致芬妮
Distributor:
Publisher:
Publishing Date:
ISBN:
Format :
Category:
Price:
我凝視手握鐮刀的你
此刻愛戀像豐收的稻穀
詩集名稱《凋零與豐收——致芬妮》,芬妮是誰?
芬妮不是謬思女神之名,卻是作者的謬思。
芬妮一詞截自希臘神話中的冥后,波瑟芬妮(希臘語:Περσεφνη、拉丁語:Persephone),又譯為普西芬妮、泊瑟芬。波瑟芬妮是一位代表豐收與植物,卻又象徵死亡與毀滅的少女,擁抱著鐮刀,手持稻穗,荒謬的組合。
詩是一封封信,在這個矛盾的時代,尋找某位讀者,或芬妮。
這是作為一位詩寫者對於詩的熱愛——莊敬,嚴肅。
這是作為一位詩寫者對於詩的痛苦——否認,割捨。
同時間也是生而為人對於生命的熱愛與痛苦。
聯名推薦
陸穎魚(詩人)
推薦好評
徐國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副主任)
楷治的詩中有兩種聲音,一是企圖透過形式的實驗,來試探詩歌的邊界;
一是在懷念與抒情中,呈現對時光的溫柔感受,二者同樣表現了他對藝術感受的執著。在晶片運算飛快的量子時代,我讀楷治的作品卻感受到舊日舒緩的節拍,像午後雨過,黃昏遲來之間,那種惹人沉思的靜謐瞬間。
陳有志(詩人)
當我靠著記憶深坐,在泛黃而偶有缺角的一張張畫面裡見到,見到那於書桌之前耐心沉思的少年,並以等量的執著聽他談論詩的隱喻和實現,談壯遊與死與生等連結自我的重要主題。我想,他是絕對痛苦也絕對充實的。在具有勢態且充滿活力的青春時期,通過易感的心靈與敏捷思想前去覺察,追索,探勘進而擁抱那些生命的重與輕。
我想,我亦是絕對痛苦卻絕對感動的。
當我們靠著記憶深坐,在楷治狂風般的撕裂與日陽般的呵護之間獲得新生的詩篇裏,我們必能與那些少年重逢——重見徘徊都市街道的自己,懷疑的自己,有傷的自己,有夢的自己,時刻感到不滿的當代的自己,而接續興起活力綻放之姿,重新前去覺察,追索,探勘進而擁抱那些生命的重與輕,擁抱那些已死將死與未死的重要主題。
陳其豐(詩人)
這是收成的時節,自馬來西亞渡海來臺,章楷治以信為槳,「用詩作舟」,追溯存在根本,探勘意識縱深。或直面相對,或托物言志,他勇於質疑,逼視青年時期的焦慮與困惑,用力發聲的同時,卻又近乎冷酷地將刀鋒橫向自我——「因為我們都知道,今夜的月光儘管隕落/明日的陽光也將劃開我們腫脹的眼」,看似凋零的表面下,有著不可輕易搖撼的堅毅與溫柔。
蕭宇翔(詩人)
《凋零與豐收——致芬妮》兼擅抒情與辯證,這兩者的和合互涉,真正昭示了詩人的宿命。章楷治進一步尋覓到一種信箋詩體,包含了詩人屬筆當下的後設自我,內外往返之間,體裁陡然擴增,如見一個世界的核心向外翻開,攤平為殼體、環帶、星雲。我們期待詩人對於節奏、句法、意象的精緻處理(或者有意掉幀),以供思維的脈絡在詩中展開,或許明白:挫敗也好,鬥志也好,只要依照一個姿勢或體式,絕對詳實,由小而大,迴還輻輳,有效地展衍,輔以有情的聲腔,與娓娓的敘述章法,人的生命、人的一切,困與逃,愛與死。這是人的歷史、人的源泉。讓詩歌使我們相信,我們能疏解一切的綁定與二元。
作者簡介
章楷治
2002年生於馬來西亞。現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三年級。曾獲創世紀開卷詩獎。作品散見於報刊。風球詩社社員。
目錄
推薦序——人人都在索取警句 唐捐
代跋:致芬妮
心臟,驟停•驟跳
你還在尋找什麼
KEDAH
無法脫離的窘迫——讀陸穎魚〈生活無可避免是政治詩〉
有燕
大山腳
日新
石頭
給Z第一封信:寫一首詩
土生土長的異鄉人
紀錄片
給Z第二封信:讀一首詩
作舟
給Z第三封信:隱喻
西西佛斯
希望
念頭
給Z第四封信:跳躍
無神論者——觀起乩的阿嬤而作
膜拜外物的信徒
給Z第五封信:保質期——觀《重慶森林》後作
每年
哭泣
初次
請將我放歸大海
豐收——觀電影《倫敦生之慾》而作
落
生與死之歌
眺
給Z第六封信:音樂
詩人之死Ⅰ
給Z第七封信:夭折的詩人
詩人之死Ⅱ
給Z第八封信:夭折的詩
向生命提問——致維克多.弗蘭克
惡——讀漫畫《惡之華》後作
給Z第九封信:毫無情感
死亡詩社——電影《Dead Poets Society》
修——參詩人楊牧紀念園區而作
給Z第十封信:實踐一種別離
後記:詩作為錨點
推薦序
人人都在索取警句
唐捐(詩人、散文家、臺大中文系主任)
A
一切詩都在「致或人」,如神,如鮮花,如頑石,如電亦如露的讀者。
詩人有時假裝在獨白,其實總渴望著不確定的心靈被觸動,生出「這是為我而作」的感覺。然而有時,詩人刻意說他在「致芬妮」,但芬妮未必有在聽,反倒是看似無關的我們,色授而魂與。啊,芬妮,永恆的受信者之代碼,謝謝你誘引一位青年詩人,誤觸天機的警鈴,使這平安的詩界忽然波動起來。
我與許多人一樣,偶然瞥見第三信,本來要當成垃圾郵件從意識裡加以刪除。但直覺——我向來的指導老師——告訴我,裡面有我等待良久的金霏玉屑:
唯我處最底端,鄰近水面足以瞥見那群裹挾信件的漂流瓶
光——透不過他們有物的軀殼,折射
海——透濕了軟木塞打濕了一篇,語言
看不清,模糊的字體渲染一片陌生的汪洋
無法得知他們自何處啟漂,何時相遇
多麼靜美而深刻的筆談,詩人緩緩攤展意象的藏寶圖,沒有狂呼疾走,沒有概念演繹,卻自有一種熏染人心的力量,詩意的雄辯。大至路線的規劃,小至路標的設置,皆具慧心,聲響之徐緩起伏自成風姿,而意義反倒退而為輔助的位置——義因聲存,道以載文,這便是音樂的境界。
在我看來,以「論詩」成名是極特別的事。
「論詩」有賴才識,但出之以「詩」,則又須具備摛藻鋪采的能耐。
楷治才二十初度,我完全不訝異他對聲色的敏銳,詩本關乎天資。但他對於詩學原理的深刻感知,確實頗不尋常。他注意到隱喻的操作過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幾經猶夷彷徨,在有無與淺深之際堅決地探索,乃能如一只瓶中信漂向不可測的某端。年輕的楷治一邊習詩,一邊願意思索詩的抽象課題,並且在第一現場向所愛的人分享他的心得。彷彿代替世間所有寫詩的人,向可能讀到這首詩的人說,我想,詩就是我寫的這個樣子。
B
整本詩集的構成是這樣的:十封給Z的信,是為論詩之詩;中間穿插關聯或小或大的篇章,彷彿做為印證。第一信便談到寫作的基本動力,「我」以為哲學與詩是必然,而「你」似乎更喜歡愛情。這兩端各有千秋,本來就難以平衡,詩人需要這種不安。第四信進一步提到「跳躍」,做為修辭技術的詩的跳躍,終究無法縮天節地,使我到達你的身邊。
這十封信既是有力的抗辯,也是一種哀愁。
不知道為什麼,楷治對於「詩人之死」的課題特具敏感性。作品脫離作者的管轄而為獨立的存在,這是第二封信的主旨,「我」閱讀經典時只知句子雕塑出來的臉及光影,也希望「你」這樣閱讀我的詩。詩人說:
在深夜裡我尋找參照物
覆足在一片充滿足跡的悼詞
在幽暗的叢林裡群吊的屍骸
肉片脫落它們升高,雕琢著一兩具白骨
脈絡,支線交織。樹冠散發光芒
像晝日的閃電,光淹沒一道光
在文字的世界裡,乞腦剜身,在所不惜,楷治論詩常有一種壯烈而崇高的語調。肉身逐漸消亡,自然秩序卻經重整,詩是一種混合的哀悼(對經典,對時間,對肉身),也是一種慶典。我有個偏見,只懂得清醒而不懂得狂迷,即不足以言詩。我喜歡楷治在這井然有致的雙行體裡,忍不住的狂迷,以及包裹在狂迷底部的銳利與堅持。
第七信和第八信都涉及「夭折」。誕生是神聖而艱難的,無論是一個詩人或一首詩;何況還須飽經磨難,乃能成長茁壯。但年輕的楷治已經看到,或者預想,假如沒有把持好初衷,詩人是很容易夭折的。同時,他決心對抗速食主義,即使受著石刑一般的痛苦。因為在詩的世界裡,「死」具有多重涵義。有時如草木之澌滅,有時重新發現了自己,有時就是生命的變形。
C
向死亡提問,向偽裝為生活的政治詩提問,向時間提問。
我知道我並不是在閱讀一位已然成熟的詩人。但他善於提問,對於詩與世界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而且還能製造警句——他認識到「比羽毛還輕盈的傷害」,而且知道必須為它找到對等的文字。雖然「在無神論的邊緣徘徊,但尊重且越發恐懼神明之下的小部分極端」。以詩再現Ubike 的鈴聲,蒐「集今古文之爭、神思、是非論、編年體、靠北、性惡論……」。
楷治來自馬來西亞檳城州之大山腳,那裡有著別樣的風土、社會與政治。
我約略感知做為異地求學的遊子,他正在以詩重構故鄉與個人的成長體驗,不免有所憂患。而且身處詩藝追尋的第一個階段,對於魚目混珠的世界,也懷有一種不滿。但他知道,詩人的憑藉終於是手上的一支綵筆,只有克制過多的情感,運用曲折而多樣的技術,才能生出與命運抗衡的力量。
因此,即便是在死亡與死亡之間,依然要講究音樂性(第六信):
我喜歡結尾,結尾的那種悠揚
讓音符成功在空氣中小幅振動,流動
流動在狹窄的音樂廳,環繞——
在不規則海綿前反射,碰撞
再度將漸弱的音符以振動加固——
在行與行的邊際,間不容髮的地方,詩人在調控著輕重緩急,以聲音去統治意義。惟有懂得蓄勢待發的道理,才能忍受空白;也惟有理解文字的的肌理,才知道怎樣切割話語,重構訊息拍送的次序。抑制那些簡截有力的聲明,叫它們讓位於看似柔弱的餘音……。
人人都在索取警句,無論懂詩的,或一輩子不曾夢見詩的。
但警句跟格言長得很像,並非所有警醒耳目的語言都可以形成美好的詩句。楷治的第三信,能在一首詩裡織進那麼多神來之筆,反而緣於他從容道來的耐心。這首詩雖專論隱喻,事涉比興,卻不乏賦筆的調節。蓋隱喻不足以自行,須賴精密而有魅力的句式乃能展布開來。而楷治的複句,思深而氣長,寫得特別好。
但我知道楷治將不會留戀於這些警句,甚至是這本詩集。他已在最後一信裡告訴芬妮,將在堆滿靈魂的書桌前,讓紙角沾附著火星,完成一種道別。
那麼,我這篇在七日間隙中草成的短文也很樂意同歸於腐壞澌盡泯滅。
2023年12月25日于龍淵刀割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