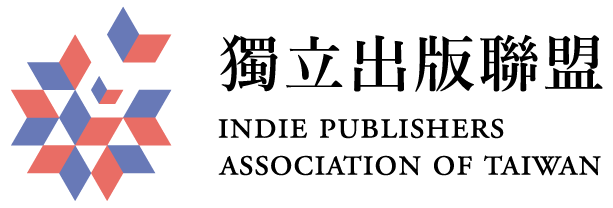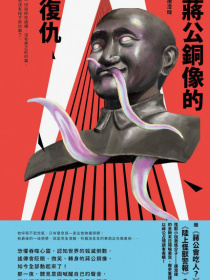《蔣公銅像的復仇》摘文
序幕
i
他提著消防斧,沿著路燈微弱的窄小街道,向中正公園走去。酒精讓他的步伐搖晃,讓他耳中充滿血液流動過快的噪音。在那些尖銳的嗡嗡聲、模糊的回音間,一段很久沒聽見的歌聲浮了上來。
總——統 蔣——公 您是人類的救——星 您是世界的偉——人
總——統 蔣——公 您是自由的燈——塔 您是民族的長城……
他很快就發覺那是自己唱起來的。沒想到在這時候,這首歌會這麼自動地、一字不差地從遙遠的記憶中跑出來。
他以前確實唱了太多次。很小的時候他什麼都不懂,就只是跟著全班、跟著全校一起大聲唱。過了很多年,等到開始覺得不對勁時,他已經沒辦法忘記這首歌怎麼唱了。
這令他感到懊惱。畢竟現在是要去砍蔣公銅像,怎麼反而歌頌起他了呢。早知道就不應該先喝酒的,一喝醉就會忍不住哼歌。他早先喝酒是為了擺脫整天下來煩躁不已的各種感覺——老闆為了省錢凹人講的鬼話、漲價自助餐裡的餿油味、下班車陣間的廢氣、以及樓裡不知道哪邊在敲的聲音。但壞就壞在不該喝酒時開電視;一看新聞,又是倒了多少店、房子有多貴,不三不四的人開著名牌車,到處酒駕撞死那些孝順兒子。以前,他覺得只要再努力一點,就可以擺脫這一堆狗屁倒灶的事,可是他已經努力到快受不了,還是什麼都沒變。
怎麼會這樣?電視上的政治新聞、新聞過後的政論節目,還有一年接一年的中央地方選舉,讓他漸漸找到了答案。造成一切不幸的淵源,就是銅像用來紀念的那個人,以及到現在還在崇拜銅像的那群人。如果當初他們沒有來台灣,或者現在他們全部消失,台灣和他自己才有變好的一天,但也因此,變好的一天還是沒來。所以現在能暫時用來擺脫這一切的,就只有酒了。
酒讓各種煩躁的感覺變得模糊疏遠,進而使他內心的念頭變得明確強烈,好比說哼歌,好比說去砍銅像。最近,兩方陣營在新聞上為了銅像越吵越兇,破壞銅像的新聞也越來越多,或許,這就是全面開戰的信號,而他也該為台灣的將來投入戰場了。想著想著,他便順手抓起一把丟在牆邊的消防斧,穿上拖鞋,推開門就往外走。
◆
隔一條馬路就是中正公園了。他便走著他自以為的直線往馬路對面去。
走到路中央時,他開始感覺右側越來越明亮,並在最刺眼的一刻響起尖銳的嘶吼聲。他往右一看,一台車莫名其妙停在他面前,車上駕駛一臉驚慌地看著他。是怎樣,他心想,靠那麼近是想撞死人啊。如果不是還要砍銅像,早就砸你的車了,還看。他晃了一下斧頭,警告地瞪了駕駛一眼,就繼續穿過馬路。
一盞微弱的小燈照出橫寫「中正公園」的金屬板,他便從旁邊的小徑搖搖晃晃走進園內。他沒想到半夜的公園居然這麼暗,只有幾個昏黃的光點在半空搖曳;他勉強認出那是燈柱上的燈光,被一堆樹枝樹葉擋在前頭。他順著枝葉往下看,發現四周全都是站著不動的人,嚇得他一瞬間彷彿都快醒了。他定神一看,原來那都只是直挺挺的樹木。
他先是覺得好笑,但又感到有點難為情。自己怎麼會這麼膽小?酒精的暈眩讓他只能抓著幾個名詞直直地想——膽小是因為黨國教育,黨國教育一直都在嚇唬人。那就只是樹,但不知道是什麼樹,既然這麼高,應該長很久了。這公園感覺很有歷史,那些樹搞不好日治時代就在了,如果不是中間硬塞了一個銅像,不然本來一定很美的……
朦朧思考中他穿過了樹林,來到公園中央。公園中央是一個圓形廣場,從其他入口穿過園地的小徑,也全都通到了這裡,而蔣公銅像跟它的底座,就像一座祭壇似地立在圓心。此時廣場一片陰暗,只剩底座周圍幾盞燈斜斜朝上,照著這尊一手插腰、一手拄著拐杖的蔣公銅像,讓它在紫色雲層下,有如一團透著金屬質感的巨大陰影。
這銅像的底座不算高。他歪歪扭扭地爬了上去,貼在蔣公身上。風越過樹梢吹來,讓他感到一陣冰涼。要怎麼砍蔣公,他其實到現在都還沒一點頭緒。他先想著砍頭,但蔣公的頭有點高,砍不著。還是砍它的腳?但砍腳好像不夠氣勢。還是砍胸口吧,他心想,胸口一個破洞就很好看到了。
他舉起消防斧,在銅像胸口輕輕畫出一道標記。斧刃擦過銅像表面,發出一陣古怪聲響,令他起雞皮疙瘩。那聲響簡直像從蔣公體內冒出來似的。他不自覺停下動作;一些模糊的往事好像隨著那發毛的聲音浮現,一些小時候大家都在傳的故事,說什麼蔣公銅像會眨眼,蔣公會對著你笑,蔣公半夜會出來巡視……一想下去,他反而縮回了手。可是沒了那聲音,眼前的蔣公又好像只是一尊破爛銅像。於是他把一股涼氣深深吸進他發熱的口鼻,抓緊斧頭,對準了銅像胸口一劈。
他以為這一劈會發出敲鐘一樣的聲響,但意外地,銅像並不堅硬也沒有彈性——斧刃陷進了一種絕對不是金屬的質感,他甚至感覺有股力量要夾住斧刃。他抽回斧頭擱在一邊,掏出手機往砍下去的地方一照,看見剛砍出的那道缺口正不停流出黏稠的液體。
銅像裡面怎麼有這種東西?算了先不管了。他跳下平台,卻感覺兩腳落在黏答答冷冰冰的東西上。他納悶而厭惡地用手機一照,自己的雙腳正浸在一灘半透明液體裡,液體還沿著腳踝一路往上包覆,一股異樣的噁心觸感從小腿直衝他腦門。
搞不清狀況的他只想趕快先踏出去,卻發現兩條腿都抬不起來,黏膩感甚至摸進了他的短褲裡。他用雙手握住右膝想拔起腿,反而讓液體順著手指包覆上來,手背上更敏銳的觸覺,讓他感覺到那液體裡有種活生生的力量,正抓住他的手往上爬。
他只來得及發出一聲叫喊,那液體就爬上了他的脖子,繼續鑽進鼻子嘴巴。他一邊看著那液體逐漸蓋住燈光,一邊感受外物強制進入體內的噁心,同時陷入徹底的恐懼——他呼吸不到空氣,只有窒息感一直往他肺裡頭鑽;他最後的一絲感受,就是完全清醒——有個活生生的東西正在傷害他,他用身體內外的所有部位,同時體會了這個事實。
ii
晚上開車時,他最討厭的就是那些亂七八糟的光源——號誌、檳榔攤、便利商店,三更半夜還在那邊亮啊閃的。尤其已經很想睡覺的時候,那些五顏六色的光還一直隨車飛舞,看著看著好像連自己都要跟著飄走了。
還有一種燈他更討厭,就是現在車屁股後面那種不知在亮什麼的銀色車燈。每天半夜都會碰到,先從後面傳來囂張的轟轟叫,接著照後鏡裡就一整片白,然後那些低到快磨在地上的車身,就會轟地一聲從旁邊加速超過他,車屁股上一道道還在閃動的刺眼藍光、綠光、紅光,便在他眼前左搖右擺地急速離去。
看著車屁股越扭越遠,他心想,怎麼不去死一死呢這些人。現在就是這樣太自由、沒規矩,什麼都不給管,才會從上到下都一團亂;特別是那些搞政治的,要不就怕事不敢管,要不就整天把錯推給八百年前死掉的人,就是沒人肯實在做事,害得像他這樣的人如今越過越辛苦。
說穿了一個字,就是亂,跟街上的五顏六色一樣難看。他很難不去懷念以前那個有規矩的時代,而他一路活到現在所得出的結論就是,一定要管。只要每個人都管好自己、管好別人,國家社會就會好好運作,就會強大。而且,最上頭一定要夠強,強到讓所有人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地服他。就他看來,夠格的人在這時代只出過一個,就是——
一道白影突然出現在前方車燈光束裡,嚇得他猛踩剎車。他驚魂未定中一看,那人居然還一臉不知錯的表情,還在那邊瞪,還瞪。但他看到他手上好像拿著一根什麼,原本要猛按喇叭的手就縮了回來。那人晃了晃傢伙又瞪了一眼,便轉過頭繼續往馬路那頭的公園走去。馬的,活太久了是不是,他忍不住在心裡罵著,並鬆開了剎車。
但他忽然覺得不對。一個人半夜拿傢伙去公園是要做啥?會不會是殺人之類的……他想了想,還是覺得別多管閒事比較好。萬一什麼都沒幫到,還惹上麻煩怎麼辦?而且都累到有點眼花了。
可是,如果真的出了什麼事,追究下去是不是他也會有責任?一想到這種可能,他便立刻掉頭,逆向切到剛剛的公園邊,加快腳步跑進入口。
一片陰暗的公園令他緊張起來,但眼睛也沒那麼花了。走在黑板樹的臭味和微弱照明中,他忍不住埋怨那些負責管理公園的官到底在幹麼。就在那時,他聽見一聲喊叫,從更前頭傳來。他立刻朝那方向跑去。
穿過樹林,他看見蔣公銅像的剪影落在眼前暗紫色的夜空下,一股刮擦聲持續從那底下傳來。他心想,說不定那人只是來砍蔣公的,如果是這樣,他反而應該先揍他兩拳才對。他抱著這樣的期待靠近了蔣公銅像,雖然看不清那人,但刮擦聲就在前方。他握緊拳頭,小心翼翼地走近——
當他覺得已經近到能打下去時,燈忽然像布幕掀開似地一盞接一盞亮起來,為他揭露眼前的真相。燈光照在一張臉上,那張臉已經像麵皮一樣拉到變形,但還是能看出睜大了眼的驚恐表情。那臉被一層膠質包住,而膠質正被什麼往上吸,所以那臉也跟著一起向上拉長,眼睛鼻子牙齒嘴唇全都像剛加進咖啡的奶精一樣,一邊變形一邊順著蔣公銅像的表面,流進它胸前的開口裡。接著向上流去的部分旁邊好像有兩隻手,接著是兩隻腳,最後是一把消防斧,拉不動掉下來又重新拉上去,就這樣反覆刮擦著銅像腿部,而不停發出毛骨悚然的聲響。
那聲響讓他兩腿發軟,跌坐地上。抬頭一望,蔣公光頭剪影裡看不見的面孔,彷彿正向下打量著他。僅剩的逃走念頭驅使他翻身向外爬,接著勉強起身,然後狂奔。他根本找不到來時的小徑,就只是拚命向前跑,撞上一棵棵發臭的黑板樹,跌倒又繼續跑,直到飛撲在引擎蓋上。他跌跌撞撞地摸向前車門,發抖的雙手摸出鑰匙,上車一發動就猛踩油門。眼前雜亂的七彩燈光瘋狂向後飛馳,耳中的聲音只有引擎的怒吼和自己的喘氣聲。好像沒有東西追過來。當他正要鬆一口氣時,一對巨大的銀色眼睛在他車前亮起,朝他撲了過來。
四周靜了下來。銀色眼睛什麼的全都不見了。只是身體不知為何動不了,頭暈得很難受。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該回家了?他勉強睜開眼,看見面前的景色全是龜裂的線條和血跡。他想下車卻沒有力氣,只能稍稍把臉往左偏一些。他看見有個人影向這頭走來,在車門外停住,一個漆黑而光滑的頭顱剪影,向前伸了進來。
他發出慘叫。
iii
房間裡每件東西都在原處等著他。他拿起掛鉤上的褲子穿好、把被子摺好、走進浴室、刷牙、洗臉。他拿起掛鉤上的毛帽蓋住光禿的頭頂,把鞋櫃上的襪子穿上、穿好皮鞋,拿起櫃門上的鑰匙、出門,沿同一條小巷到公園邊上的市場吃同一家早餐。
他不太去區分這是今年、去年還是更久之前的某個早上。他至少也得從某一年開始分不出來,但既然都分不出來,是哪一年也不知道了。他知道自己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但他不怎麼擔心。分不清過去和現在,就感覺不太到日子有在變少,在那之前,人還能動,每個月還領得到薪餉,這樣就夠了。
在這些分不清的日子之前還有一些回憶,他已經記不得細節,但他清楚知道那些事只發生過一次。打仗。子彈像口哨一樣拔尖飛過他身邊。砲擊從遠方震動著他的身體。聽見信號之後,向前衝,或者向後逃。滿地不成人形的屍體,行軍行到只有雙腳還醒著。那些事都只發生在確切的某一刻,但會不時潛入那些分不出來的日子,讓他在某個下午、深夜或清晨突然醒來。
構成他生活的這兩種時間感,在他心中始終有一道清楚的界線,直到那天半夜。一聲沉重的巨響令他反射地做出防禦姿勢,但跟不上意志的身體,讓他發覺自己並不在戰場上。他手邊沒有步槍,只有房間裡的東西在原處。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能吃力地起身,然後三步併兩步地,套了雙拖鞋就走出門。
外頭一片漆黑。路燈下,兩台變形的車在對街扭成一團,一股白煙冒著。不得了了這,他心想,快看看車上的人。他踏過滿地的碎零件,朝較靠近的駕駛座走近一看,這可慘了,人卡在座位上,血又流成那樣,要他說的話,大概沒得救了。
他正想再去看另一車的人還有沒救,面前這人卻抽搐著轉過頭來,瞪大了眼睛。看著那逐漸蒼白的臉,他倒也不害怕,這種事以前太多了。他把頭湊過去,想聽聽那人還有沒有什麼要交代,但那人突然慘叫起來。
「不要過來啊!……蔣公……」
突然聽見這兩字,他一時還反應不過來。這怎麼著?誰死不是哭爹喊娘的,哪有人喊老總統,是不是自己聽錯了?他忍不住把頭伸進車窗,看能不能聽清楚這人到底在說些什麼。
「不要……蔣公……不……」
然後那人就沒聲音了。
他想不透這到底怎回事。他不自覺抓了抓頭,才發現出門前忘了戴毛帽,襪子、皮鞋、鑰匙啥都沒拿。全都亂了套了。
延伸閱讀
怪物餵養的少年長大後──專訪陳夏民X唐澄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