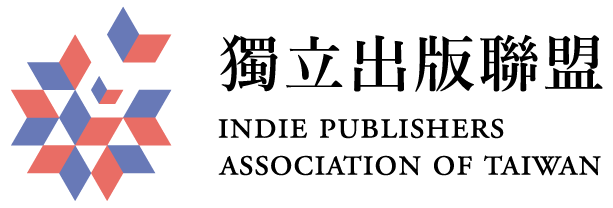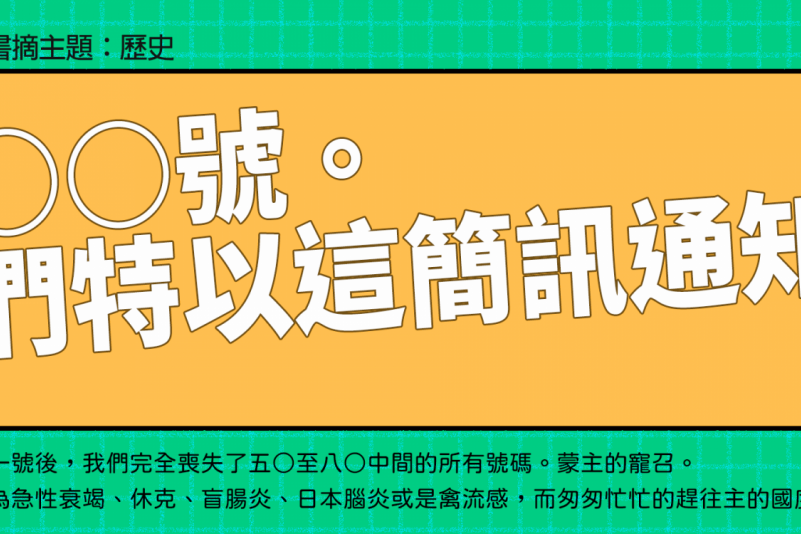
馬芳的位置就在辦公室進來靠門口的地方。在除舊布新的新年前夕,她在玻璃門上以噴罐寫下祝福我們的泡沫字體。一株壞了幾顆燈泡的耶誕樹還立在門邊,閃著殘缺的光線。樹下的飾品她還不肯收拾,散落著成堆的塑膠麋鹿還有保麗龍禮盒,掛在牆邊的雷射彩帶七零八落,老是絆住經過的人的腳,引來一聲驚呼。
這個女人是不是太閒了呢?她雙手攙扶著美耐板置物櫃緩緩起身,將全身重量交由櫃底的四個滑輪引身而立,屁股朝著這頭伸了一個懶腰,露出裙子與襯衫中間那一塊皮膚。不。那不是皮膚,而是一種肉色的束腹。又打了一個哈欠。走過她前方的人抱著一疊卷宗,弓著身子以下巴緊緊壓住。會不會有人這樣想,我這個主管交待給她的工作是否少的別有用心。她雙腿開開的在那裡扭來扭去,什麼體力活動讓她如此疲累?我想不通,也許是連假前的耶誕布置活動。她抬起一隻穿上絲襪的腿,拉直那貧瘠的曲線,似在專注感受下盤的肌力有何不對勁。沒有引人側目的問題,我肯定她本來就想要引人側目。
「偷偷摸摸的在聊什麼?」新的標籤在螢幕底下閃爍了起來,鮑伯兩個字要求加入了這個談話。
「鮑伯,看看這個新聞。」我說,「在一九五九年美俄冷戰期間,一艘名為致敬號的前蘇聯太空船殘骸,將在脫離衛星軌道後的三十八年後,再度回到地球上空,與一九九六年中國發射導彈擊落的氣象衛星殘骸H207會合,成為離我們地表最遠、最大的太空垃圾群。妳剛剛對這件事是怎麼想的。馬芳?」
「在經過巴布亞新幾內亞後,」馬芳說,「我們會是第一個看見它飛越上空的華語系國家。」
漂亮,我和馬芳是多麼有默契。鮑伯完全不會相信上一秒我們正在講他的壞話。
「而且猜看看那會是什麼時候?」我說。
「跨年當天,或當夜。」馬芳回答。
「我也覺得是百年那個晚上。」鮑伯說。
「沒錯。」我說,「你們兩個還真有默契。我再告訴你們,我從新聞上知道這些垃圾有什麼。一顆美式足球、鄧小平題字的推進器外殼、林肯號太空站解體後的碎片,包含太空人所帶上去的日常用品。開罐器、原子筆、附框的相片、腸胃藥、消炎貼片、一隻太空犬的骨灰罈(為了紀念第一個升空的哺乳類動物)、俄羅斯套娃、鈔票、藤球、果戈里的小說、杜肯大學籃球隊的球衣、貓王的唱片。這些大至幾公尺,小至只有五公分的垃圾全有編號及追蹤,但全攪混在冷凍的鍍膜鈦金屬塊中飛行。」
「真驚人。」
「這些垃圾以二萬五千多公里的時速在我們頭頂上空加速再加速。你們可要看仔細了,當天晚上它劃過我們眼前的速度快的像流星雨。」
「真難以置信。」鮑伯說,「每秒可以飛行七公里的一本書。作者知道這件事嗎?」
「誰?」
「那本小說的作者。」
「果戈里?他已經死了。」
「幸好他已經死了。」
「死一百多年了。」
「否則他會說不出話來。嘴巴張得開開的。」
「以前的人很容易受到驚嚇。現在的人則不會。」
「從前的人以為天上有神。要是我也會嚇一跳。」
「真的很好笑。」
「沒錯。」
「如果有神,一個好女人為什麼不值得被珍惜,男人一個接著一個跑掉?」
「也有道理。」
「根本沒有那玩意。」
「你說的對,鮑伯。那上面沒有空氣,沒有空氣的話就什麼也沒有。」
一○○號。我們特以這簡訊通知你,隱居在捷克華沙,西瓦‧沃拉村東部小鎮一處地窖裡的七十六號,已在數天前死於併發肺氣腫。繼六十一號後,我們完全喪失了五○至八○中間的所有號碼。蒙主的寵召。他們因為急性衰竭、休克、盲腸炎、日本腦炎或是禽流感,而匆匆忙忙的趕往主的國度。成為祂在天上的牧者。我們很擔憂,因為這些徵兆祂並沒有事先通知。這麼多的意外在這個年末被召喚出來,究竟是為什麼?一○○號,我們有預感你將是下一個。你是國度裡頭最年幼,也是成就最高的號碼。跨越了時間的長河,見證祂在地上的奇蹟。那日子很可能在新年前後就會到來。一○○號,你是怎麼想?
我一口氣刪了手機裡一大串無用的資訊。未接來電、通話記錄、瓦斯費語音通知、恐嚇我的不明簡訊。數則有關司法機關、連線設定過期、車禍以及中獎的詐騙簡訊。數則有關爸爸在療養院復健進度的通知、五則低利貸款的優惠、一段來自國外的恐嚇簡訊、只有背景而沒有人說話的錄音留言、印尼籍看護工的特價合約、一則預祝新年的動畫、一張似乎是從一處昏暗室內傳出的圖片,上頭有一個面目浮腫狀似噎死的外國人臉孔。
手機只需留住這個簡潔有力的流線型外表、沉甸的鋁鎂合金外殼,以及二十種左右的應用程式即可。那是最完美的狀態。曾經有人為了手機上需不需要天線而出現爭論,不用說,我當然反對這多餘的東西。趨勢也證實了這種走向,連手機上的按鍵都令人困擾、如今的訊息量已是過去的數千倍,我們只需留下重要的東西,就像手機需要時常清空,不要留下任何陰謀、詐騙、或處處引誘人的陷阱檔案一樣。
書籍簡介
 《百年》許倍鳴
《百年》許倍鳴
《百年》小說裡的角色陳何,他是個天資聰穎,腦部早熟的兒童,生活且工作在台北。某天他開始收到不明發訊者的簡訊,宣告他的死亡將至,並擅自開始倒數。呼應事件而不斷出現的台北摩天大樓,最終成了作者埋設其中的符碼。到底陳何是如何行渡於虛幻與現實中,直至死亡的降臨?
如同卡夫卡《審判》裡的K,陳何的抵抗是一連串自疑與掙扎的過程。他也同他身邊一個個接連落入衰老、疾病、或是婚姻問題中的成年人一樣,越接近威脅本身,行徑越發荒腔走板,不能自己的自衛反應更顯無力而頓失意義。
「合理」的場景或者並不存在,但小說家期待的也不是個合乎烏托邦的劇情小說,而是更加接近後現代語境的文本。企圖以各種變調的訊息與場景來展示台北。那些和現實總是脫鉤的廣告,毫無意義卻也如實地構造了我們所處的世界。電視媒體的、網路訊息的、文字的,大量的垃圾訊息總是試圖淹沒主角的聲音,致使角色成了一個破碎、斷裂、身世模糊如同人工造物的人物,遊走在以虛妄與想像的方式存在的「台北」,竟是如此真實的現實之地;也是它,存在於你我之間的「台北(台灣)想像」,形塑、實現了我們的面貌。正如小說最後一章某段文句的暗喻一般:
「我想說,台灣,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地方,並且不是一蹴即成的。一百年。它經過了這麼久。終於把各種不可思議都給實現了。」
我們都被不可思議的實現了!
延伸閱讀
從黑暗中閱讀的童稚之眼中,我們看見了什麼?太陽王路易十四成就凡爾賽宮背後的動機為何?你知道肛塞本來是用來治療的工具嗎?代代相傳的排灣族口傳歷史,與日本外交文件及當時新聞報導有怎麼樣的不同見解?六月書摘專題:讓我們從歷史看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