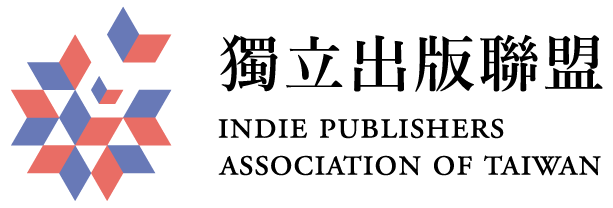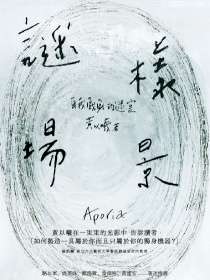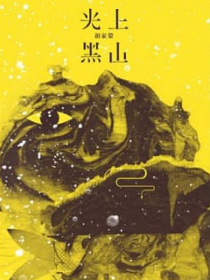文:洪七
「詩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座談一開始,黃以曦就直接切入主題,提到了孫與胡兩人的詩觀點幾近「水火不容」,於是分別問了兩位詩人,詩對他們的意義為何?
「詩是毫無意義的東西。」接到問題的孫得欽,擰著表情幾秒後回答。他說他以前確實覺得詩重要過,所以曾花了時間練習,畢竟詩有些形式和規則存在。詩曾經帶著他走向某個地方,但就在某個崁、某個時間點,他突然覺得詩不重要了。
「但正因為覺得詩不再重要,所以後來才能寫出一堆東西。」孫得欽說,他上一本書是花了十來年才寫了幾十首詩,然後再從中篩選出三十首。但後來跨過了門檻後,他發現他寫的東西更貼近自己的呼吸與生活,一下子就寫了上百首詩。他說,現在他並不會特別覺得詩特別重要或不重要,但詩是貼近自己的。當自己的生命改變時,詩也會跟著改變。

黃以曦認為,雖然孫得欽講的雲淡風輕,但當他說「詩以前很重要,現在不重要」,其實意味著他有在思考什麼是「不重要」的。
黃以熙說讀孫得欽的詩很有趣,因為他一直在解構自我,解構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的。她覺得孫是很細膩的詩人,他的語言可以同時展現神聖和惡魔很兩極的存在。
黃以曦在講座中念了孫得欽的其中一首詩:
〈這是好的〉
生命好大
去說
「只有這是好的。」
完全是浪費
黃以曦認為這些年孫得欽的詩朝向抽象的、深刻的方向而去。她說也許是因為生活太苦、太重、太難,所以到了盡頭後發現生命其實是簡單、純粹的。
「所以難的不再是那些有挑戰性的東西,真正難的是那種純粹、是那種所有光色都混在其中的那種東西,所以他的詩和前一本比,變得很簡單。」黃以曦說:「在這脈絡來說,他的詩其實是很難的。」

「詩是我在地上的工作。」 努力讓詩人現身的胡家榮
和孫得欽對詩的態度相反,胡家榮劈頭就說:「詩是我在地上的工作。」他認為,並不是只有賺錢才叫工作,工作是人一輩子都在做、可能是你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胡家榮出詩集的過程也截然不同。他第一本詩集再三年的時間就寫完了。但最新的詩集《沒有一天的星星和今天不一樣》卻是他從碩士班開始累積,經歷過一連串一直寫不出來的過程,過了十來年才終於完成。
過往他本是「靈感派詩人」,非常倚賴靈感來寫詩。後來他發現一直等待靈感來臨是不行的。他說他曾和黃以曦在進行筆談,收錄在《尤里西斯的狗》裡頭。他們談了「靈感」與「詩人的誕生」等議題。胡家榮說當時黃以曦很敏感的就感受到了,問:「通常都是先有詩的誕生,才有詩人的誕生,而你卻先提詩人的誕生?」
胡家榮說這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後來也決定不能只靠靈感寫詩。他回憶到,在研究所時期,他曾和黃柏軒、孫得欽等人組了一個詩聚會,先定詩題再寫詩,而非等待靈感來寫詩。而當時寫的詩有幾首也收進了這次新出的詩集裏。
胡家榮說,現在他很努力寫詩,比從前都還認真地寫,希望讓詩人能現身。

《尤里西斯的狗》對孫、胡二人都是重要的書籍。孫得欽說這本書是《白童夜歌》的說明手冊,胡家榮說他曾把這本書當作最後的創作出版品。
生命中的沉重與失重 談詩的懸浮感
《沒有一天的星星和今天不一樣》中有一個章節紀錄著胡家榮諸多的夢境。這些夢境紀錄對胡家榮很重要,但在書寫時,他卻有所思考與掙扎。「那時候很好奇,這些夢算是詩嗎?孫得欽可能覺得這不重要。後來我聽到有人說,是不是詩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寫的是否夠好。」
胡家榮說有多作家都會處理夢,但大多是當素材用,不會直接寫出來。但他這次是直接把夢記錄下來,放在詩集裏,他說這是他最大實驗。
對於胡家榮的詩集與夢,黃以曦在講座上直接念了詩集中的一首作品:
〈夢之八〉
弟弟找到一份文件,是四兄弟的資料:大兒子叫連家適,八歲失蹤,尋獲遺體。四人中有一人失蹤更久,從年齡和照片推測,他是我弟。
我給我爸看,我爸看出那是偽造的。
黃以曦認為這些夢境聽起來很像是電影或故事的設定。這些文字表達出的意境有「懸浮感」,是一種有重力、但又同時失重的狀態。她認為只有詩能表達這種狀態。
詩集或是身心靈作品?孫得欽談那些生活中不知如何是好的片刻
孫得欽最新的詩集被某些讀者說很「心靈雞湯」,甚至有人開玩笑的冠以「身心靈作家」的稱號。黃以曦說如果自己被這樣稱呼,她會很生氣。她說藝術家心中都有黑暗的一面,而他認為孫德欽這本詩集雖然裝得很清高,但其實很黑暗,甚至比他年少時被慾望所捆綁時更為黑暗。
她說孫得欽的詩集當然還是有描述一些神聖、崇高的的事物。但正是因為這些神聖、崇高有了輪廓,反而就更確立了有一個黑暗在那裡。她認為《白童夜歌》並非是身心靈作品,反而會為世界帶來惡。她說:「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喜歡得欽的詩,他很黑暗、且危險。」

而關於「心靈雞湯」、「身心靈作家」的稱號,孫得欽說當初有人看了詩集後覺得這本詩集很黑暗,這樣的評價一開始他確實感到有些驚訝。
但他後來仔細想了一下,他的確有留下一些黑暗的東西在文字裏。孫得欽表示自己並非是一個正向思考的人,他認為真正的正向並不是屏除黑暗,而是即便黑暗在那,你也盡可能不被影響。
他說他如果要寫一本身心靈的書籍,他的文字肯定不會被身心靈作家好。他認為正好是詩這種表達的方式,可以表達出生命中某些沒有定解的曖昧狀態。他認為黃以曦「懸浮」的比喻很準確,生活中有很多狀態是懸浮的,是無法判斷、沒有辦法判斷的。
所以當黃以曦念了一首〈這是好的〉時,孫得欽馬上提到了詩集的另外一首詩〈是好〉:
一切都是好的
是嗎?我試著接受那些
我不能接受的但失敗了
我抱著這失敗
撫摸著
像摸著
一隻貓不知如何是好。
孫得欽說有讀身心靈的人一定都知道,這些書籍常常說一切都是好的。但實際生活卻並非如此,所以他便寫了「不知如何是好。」
夢比現實更真實 易感易怒下強大的溫柔
提到懸浮感和黃以曦念的〈夢之八〉,胡家榮說這作品能被念到,他感到非常高興。這首詩在詩集還在編輯之時曾被編輯刪除,後來是在他的央求下,才把這首詩放回詩集裡。
而他會希望把這首詩放回來,是因為這首詩對他來說很重要,帶給他很強的現實感。對他而言,夢是真的,現實是假的。
他說,他就讀研究所時,明明過得很快樂,卻在那時得了憂鬱症。他也得了類風濕性關節炎,然而家族卻沒有遺傳病史,他生活的環境也很正常。現實的這一切都讓他感到不真實。反而是在夢境中,他都能找出因果脈絡。在夢中,他是高中時得到憂鬱症,那是他最不愉快的時期。
因為這些狀況,他經常自問活成這樣是怎麼回事,感到奇怪難解,所以他後來決定無論這些夢境算不算詩,他都要將夢放進詩集裏。

在這本《沒有一天的星星和今天不一樣》詩集裡頭,夢的篇幅佔了大半,而這些夢又一半是在書寫母親。
胡家榮的母親在他小六時過世,而這一直影響他到現在。他說,夢中母親都沒有死去,經常突然現身夢中,告訴他這幾年她去了哪裡。
黃以曦認為胡家榮在精神與身體上都受了很多苦,得了躁鬱症、經常失眠,易感易怒。但在他的詩中又能感到強大的溫柔。她說自己總能在他的詩中找到和胡家榮現實中相類似的印證。
她回憶了之前和胡家榮約見面聊天的過程:由於胡家榮日夜顛倒,醒著的時間和一般人不一樣,他的時間會變化、移動變化。他曾跟黃以曦說希望一個月後,醒著的時間會移到日間,屆時就能約在早上見面。
後來他們約在早上七點的星巴克,那時胡家榮早已坐在店內。黃以曦描述,當自己趕去赴約的時候,除了匆忙的上班族與學生外,她看到一抹金黃色陽光打在胡家榮身上,他整個人沐浴在光裡面。她說:「(當下有)他那個時候就在這裡的感覺。他就像一個精靈,他好像身在現實當中,卻也不完全身在現實當中」。
另外,黃以曦也觀察到,像是胡家榮其實也很著迷超級英雄的電影,也毫不掩飾對蓋兒加朵的喜好。她覺得,為什麼有一個人其實是可以享受世俗,但又經常為抽象的精神世界所困。而這一切能夠從胡家榮的詩中找到印證或辯證,黃以曦覺得這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
原文出處:洪七與源太太的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