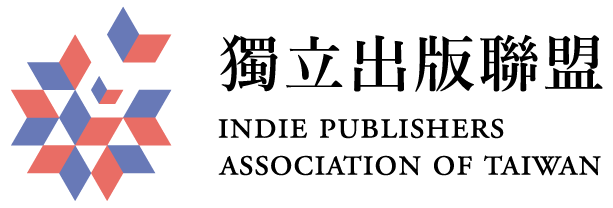我們將找到聲音,破解時間的謊言。
《這古老的兩者》是悼念之作,也是一場追尋「我」的旅程。死亡不會讓情感結束,而是以之為起點延續。但在死亡之後,對於死者,「我」將會是誰?對於生者,「我」又是誰?何杉在詩歌中多次的詢問「是誰」,追問時間與生死之間的情感關聯,也追尋萬物的本質是「什麼」?
誠摯推薦
悲悼除非訴諸語言,否則什麼也做不了,『已發生的』生命中的悲劇事件——死亡,是留給生者的債務,於是悲悼作為辯護也是一種代言。——詩人,宋琳。
真正深刻的哀悼,不是越過死亡、遠離死亡,而是讓死亡銘刻悼亡者自己的生命——留下「你在世上的殘響」,最終孕育出「後喪失」生命的珍珠——翻譯家、詩人,得一忘二。
作者簡介
何杉
本名王哲。
父親.寫作者.教師
一九九五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二〇一六年取得教育學碩士,二〇二五年獲頒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學位。
二〇二〇年,作品《未至之境》發表於《單讀25-爭奪記憶》。
二〇二一年,獲得新加坡金筆獎詩歌獎。
二〇二二年,第一部詩集《一個時刻》由新加坡新文潮出版社出版。
二〇二三年,第二部詩集《平庸之作》由臺灣爾思出版社出版。
二〇二三年,組詩《悲歌》發表於《今天》第一百四十期。
二〇二四年,《一個時刻》入圍新加坡文學獎「最佳首部作品」提名。
二〇二四年,《平庸之作》獲得新加坡文學獎「華文詩歌獎」,本書同年參展德國法蘭克福書展。
目次
語言是我們的疆界 8
▘ 真 相 25
Ⅰ 在墓前 26
在墓前 29
在果園裡 32
在某地旅行 34
在旅途中 36
Ⅱ 煙之書 38
圖 景 40
獻給二十七個生命 42
今日小雪 44
大 雪 45
煙之書 46
Ⅲ 朝聖者 60
我希望成為一隻瓶子 62
樹的紀事 64
重逢之樹 67
預言之樹 69
微觀之物 73
朝聖者 78
▞ 善變之物 93
Ⅳ 這古老的兩者 94
這古老的兩者 96
貧窮的冬天 104
Ⅴ 柑橘暮年之歌 112
另一個 114
寫 115
蛾 116
蛛 118
螃 蟹 120
像一具標本 122
雜 耍 124
我兄弟是個裁縫 125
菜市場 126
男孩們的童貞 127
柑橘暮年之歌 130
偶然性 134
針對性 135
不對稱性 136
多樣性 138’
不確定性 140
Ⅵ 起 源 142
小鎮紀事(一) 144
小鎮紀事(二) 145
小鎮紀事(三) 146
大 宅 147
村莊以外 149
起源 152
Ⅶ 大 師 164
大 師 166
懷念人們 168
如何學會整理 169
禮 物 172
溺水者與拯救 174
誰帶我的靈魂同行? 176
一間屋子沒有臉 179
睡眠.拼圖.遊戲 181
節拍器跳舞 187
Ⅷ 荷 蘭 192
荷蘭:一 慈悲街 194
荷蘭:二 海蝕 195
荷蘭:三 旅行證 198
荷蘭:四 圖書館路 200
運河素描 202
Ⅸ 普通快餐 214
啞 口 216
舊教室 218
審 判 219
倖存者看見…… 220
看 畫 222
看 守 224
隱 語 228
勇 氣 238
在夢中 240
普通快餐 241
▟ 一封信 243
▓ 一起從末日往回走,懷著地獄活下去 244
序
節選〈語言是我們的疆界〉/宋琳(詩人)
對一首正在寫作的詩而言,語言從來不是現成的東西,過去的經驗不再其起作用,即便是處理「已發生的」,構成文本的諸元素在效果上卻應該是「從未有過的」。 「站著的真理從未授予我們/什麼語言」〈運河素描〉,墓碑站著,這生與死的邊界也像徵語言的邊界,是的,「站著的真理」如此肅穆,不容爭議,它過於明白曉暢,不需要增減任何東西,而詩的真理喜歡躲起來,像復活節的彩蛋,不那麼容易被找到,詩的真理存在於尋找的過程中。中年是轉折時期,要麼放棄,要麼聞天命,在寫作中倖存,即在語言的新發明中倖存。中年的但丁迷失於「一片幽暗的森林」,在我看來象徵著所有詩人可能的共同命運。荷爾德林在《漠涅默辛涅》詩中哀嘆:「身處異域他鄉/我們幾乎失去了語言。」如此嚴重的喪失對於語言這一「危險的財富」的持存者——詩人而言是致命的,這種異域感在我們這個快速變遷的時代,即使你從未離開本土,也能被體驗到,詩人無疑都屬於廣義的異鄉者,遭受失語症的折磨,於是,何杉應和道:「暗黑取代了語言」〈運河素描〉。
詩人寫作絕非詞語的個人遊戲那麼輕鬆,屈原「道思作頌,聊以自救」《九章·抽思》是流亡者的自畫像,也預示著後世代代詩人在大地上漫遊時身上的重負。何杉在一則筆記中則說:「旅行在異鄉是現代人的生活常態;生活在異鄉是一種選擇;移民到異鄉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一棵樹將自己拔起來,抖落簌簌的泥土,其中的痛無法用數字計量。」這段話可以當作他的自作紓注,他在新加坡的移民生活堪比自我流放,如同一棵樹在遷移中的冒險,能否倖存下來是不確定的,寫作乃嘗試著重新紮根的自救行動,其中對抗虛無和遺忘的方法,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說即「捍衛熱情」。詩人是言者,也是他者的代言人,失去言說的熱情即失去了職業性,失去與世界對話的基礎。無論遭逢何種境遇,詩人都要保持「有話要說的」的姿態。我以為何杉的詩學宣言可以用下面這行詩來體現:「我有些話/要對這個尖銳的世界說」〈盈餘〉。移民生活將彼此陌生和冷淡的世界植入內心,「這古老的兩者」要並存與融合,必須勇敢地建立起同「尖銳的世界」的內在關聯,此時改變言說方式便是首要的,不可迴避的,「異域感改變的是沉思本身」(列維納斯),而異域的詩學沉思總是帶有急迫性。
節選〈一起從末日往回走,懷著地獄活下去〉/得一忘二(詩人、翻譯家)
傳統的悼亡文本通常是一種「處理」或「對應」,本質上是對自我創傷的調適與解脫,依然遵循著某種進步敘事。但何杉的詩集《這古老的兩者》,儘管顯然屬於悼亡詩,卻走向了另一條路徑。這不是俄耳甫斯般試圖自冥界帶回亡妻的努力,而是選擇「懷著地獄活下去」〈朝聖者〉。因為詩人認定「每個人和死亡都是等距的」〈睡眠拼圖〉,所以他放棄了對「解脫」的期望,將喪失作為倖存者的生存要素,深深嵌入「後喪失」的生活之中。
所有悼亡的文字都在更有力地證明悼亡者的無力感。無論詩集中的九章如何編排,墓前、旅行、樹木、遊歷、碎念等,都只能是一種「非線性悼亡」的路徑,我們無法將它梳理為一種進步敘事。只有開始的一點是確鑿的:〈在墓前〉確定了一種喪失:「你停滯,一個賽末點」。這本詩集的行程,始於人生一場競賽的結束。從此,詩歌主角你我間的相隔只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問答:「我將會問:哪裡?哪裡?而你回答:過來,過來」。詩人的策略是架構一種新的相遇:這就是詩人的悼亡策略,重建一種現在,並將它嵌入生者的生命之流。
這本詩集中對「現在」的執著,成為詩人存活的最根本動機:「現在閃現,現在消減」〈微觀之物〉。 「後喪失」的「現在」是煉獄般的。詩人寫道:「看著自己向外流淌,/傍晚的傷口裡,夜流淌著」〈煙之書〉。傍晚成為傷口,夜間從中流出;時間也是倒流的。死亡從時間中滲出,詩人無法或也沒有試圖阻止這裂口,而是凝視它的滲透與吸附,讓它成為生活肌理的一部分。這種悼亡策略,不是為了修補「失去」,也不是為了「復原」什麼。死亡無法逆轉,只能被接納。
於是,詩人以近乎溫柔的堅定,將對亡妻的追憶變成一種腹語。詩中,我們很少讀到典型的悼亡模式:哀慟、哭訴、緬懷、控訴死亡的殘酷與不可挽回。相反,他用詩性語言,將死亡「折疊」進日常。最深切的悼念不是獨自哭泣,而是「帶著她的記憶」繼續生活:「現在我只擁有道路」〈這古老的兩者〉。當然,「擁有道路」並不意味著有前進的可能,而只是有一個不停下的條件(condition)或條件作用(conditioning)。人必須活下去,詩人必須走下去。然而沒有同行者的「走」,就只是「一起從末日往回走」〈倖存者看見……〉。 「回走」不是前行,但詩人卻又必須相信,在這「回走」中:「一切洋溢著非來不可的解放」 〈倖存者看見……〉。
詩人反覆使用「旅行」、「行走」、「返回」這類意象:〈在某處旅行〉、〈在旅途中〉、〈朝聖者〉、〈荷蘭組詩〉、〈運河素描〉皆可歸入「重行」的範疇。也許亡人停在了某個身外的終點,而詩人卻邀請亡靈重新走一遍曾經的路。這種精神性的重行,既是詩集最具哲思之處,也是最深情的悼亡方式。「懷著地獄活下去」,意味著懷著親人的靈魂,即便這本身就是地獄,詩人依然願意以這種形式與亡者「同行」——一次精神的、象徵的、虛構的朝聖,借助書寫,讓詩人穩定了依然屬於兩者的「後喪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