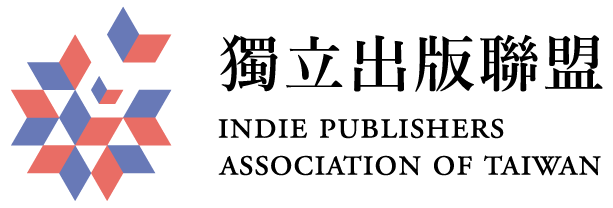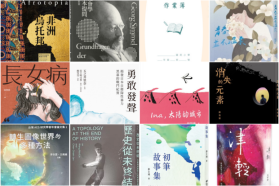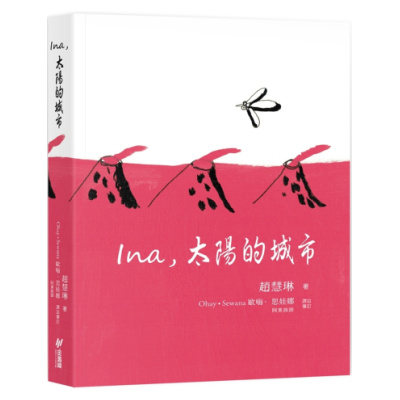
作者從離散平埔女性的跨族群觀點,貼近追尋都市原住民五十年來遷徙足跡,與讀者們一起看見臺灣最大原民族群的縱谷和海岸阿美,於當代激流中合譜,既溫柔又偉岸的都原大河大海史詩。這部作品是要印證,原鄉記憶鑲嵌在每位邦查城鄉移民生命深處的文化母體,是支撐都市原住民社群開創都市部落的最大抵抗力量源頭。
《Ina,太陽的城市》是報導,信件,論述和歴史小說的混合體。這同時是ㄧ位歴經離散的平埔女性作者,和城鄉移民的都市部落邦查ina(母親)及mama (父親)們相遇相惜,貼近追尋他們三代族人西遷足跡,再從跨族群觀點不自量力地下註腳:由臺灣最大原民族群的縱谷和海岸阿美,於當代激流中合譜,既溫柔又偉岸的都原大河大海史詩。
當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已是久遠以前的街頭記憶。當都原居住權抗爭的烽火漸平息。又當都市原住民的底層勞動分工和板模營造角色,漸為東南亞跨國移工取代。這本非典型歴史小說的撰寫者也跟著沉潛為尖齒的挖洞地鼠,深掘開來邦查都原的原鄉胎記,都市傷痕,功虧一簣營造英雄志業,和你們 / 我們也曾經是跨國勞動輸出者的微型民族誌。臺灣都原歴經過漫長的苦路,僅只換成了跨國移工後續背起的社會不平等十字架。苦難沒有消失吶。勇氣沒有消失吶。
邦查是母系平埔在後殖民年代的姐妹族裔。《ina,太陽的城市》也是跨族群乳房群山和陰道長河為筆為語言,喋喋不休,絮絮私語,在都市邊陲的文化斷層帶上趁隙開花的女性方言之書。
作者簡介
趙慧琳
1964年生,台中人,台大哲學系畢,美國愛荷華大學教育設計與技術及攝影藝術雙碩士,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早年任職聯合報綜藝新聞中心攝影記者及文化版文字記者,以〈文化家園重建〉〈新興的潮流:國民美術〉以及共同撰寫〈另類西施檳榔西施的文化觀察〉等系列報導,陸續獲得吳舜文新聞獎文化專題報導獎。
著有《有我照你:埔基愚人們的在地化長照故事》和《暗室裡的光:勵馨走過三十年》這兩本紀實專書;以及平埔多族群歴史小說《大肚城,歸來》。
她是行動,研究,寫作,三合一的社會作者。
趙慧琳《Ina,太陽的城市》創作簡介
始自民國五О年代末,東臺灣花東地區的Pangcah平地原住民,因著原鄉土地大量流失,以及西岸都會區快速工業現代化,陸續開發建設的經濟驅力,成為第一代原住民城鄉移民。他(她)們淪為都市底層勞工,遊牧營建工地的許多Pangcah板模工,在居住不正義的狀況底下,展開非正式聚落的自力營造。都市Pangcah們從溪洲闢地種菜,搭建工寮——打鹿岸,一直到頭目選舉,聚會所興築,部落年齡階層重組和豐年祭舉辦,一步步誕生了沿水而居的多處原住民都市部落。
都市治理者眼中的原住民違建部落,亦漸次成為官僚強迫拆遷的「都市之瘤」,大台北地區三鶯,花東新村,溪洲和撒烏瓦知等Pangcah都市部落在幾年間,先後面臨拆遷威脅。揚起原住民居住正義旗幟的都市空間運動興起,草根動員的反迫遷抗爭引發各界關注。官民從對峙到協商到拆遷安置或是替代方案多樣提出的十餘年間,流動於原鄉和都市部落之間的Pangcah們,又不時身處火燒,水患交替的諸多部落存亡危機當中。
《Ina,太陽的城市》則是以這樣的壯濶族群遷徙史詩為核心內容,文字顯影都市Pangcah在過去幾十年間的流動腳蹤;其中亦穿插有,從日治到國府遷台早期,Pangcah先前歷史階段承受文化殖民,導致族群關係不正義的複雜糾葛歷史源頭。(2016年專案成果摘要)
目錄
【出版緣起】
從遷徙到扎根:
書寫都市阿美族的族群記憶/林淇瀁
推薦序/歐嗨.思娃娜(Ohay.Sewana)
作者序/趙慧琳
誌謝
邦查遷徙的部落地圖
一.作者的證詞
二.吉能能麥都市部落家譜
三.民國五十到六十年間:原鄉
四.民國五十到六十年間:再見原鄉(上)馬太鞍
五.民國五十到六十年間:再見原鄉(下):太巴塱
六.民國六十到七十年間:流動-原鄉/都市
七.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年期間:出國
八.民國七十到八十年間:都市男/女英雄
九.民國七十到八十年間:都市部落(一)工寮暗夜
十.民國八十到九十年間:都市部落(二)八姐妹.水火
十一.民國九十年後:都市部落(三)祖靈石
十二.私函延藤教授
附錄
一、阿美族語的漢譯對照表
二、都市/原鄉部落名稱的漢譯對照表
三、阿美族名的漢譯對照表
四、吉能能麥都市部落家譜
出版緣起
從遷徙到扎根:書寫都市阿美族的族群記憶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林淇瀁(向陽)
二○二五年,乍暖還寒之春,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迎來第54部作品。這部長篇小說《Ina,太陽的城市》係由趙慧琳所著,於二○一六年獲得補助,二○二一年結案,又經多次擴充、改寫,終於完稿並順利出版。一九六四年生的趙慧琳長期投入平埔族、原住民族的生命史挖掘,著有紀實專書《有我照你:埔基愚人們的在地化長照故事》、《暗室裡的光:勵馨走過三十年》,以及平埔族群歷史小說《大肚城,歸來》。她也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曾任《聯合報》綜藝新聞中心攝影記者、文化版記者,並以她的深度報導榮獲吳舜文新聞獎文化專題報導獎。
《Ina,太陽的城市》是一部融合報導、信件、論述與歷史的長篇小說。趙慧琳以她身為平埔族後裔的生命經驗,透過田野調查,與來自花東縱谷的光復鄉、瑞穗鄉、玉里鄉及台東長濱鄉的Pangcah(漢譯邦查,指阿美族)相遇,並深入都市部落Cinemnemay(漢譯吉能能麥,今新北市新店溪沿岸),追溯他們自一九六○至七○年代的西遷足跡,見證他們從一九七○至二○○○年的都市部落生活。這些族人如蒲公英般離開原鄉,攜帶身體記憶中的文化基因,在都市依水而居,自立造屋,拓墾生存。這部小說寫出他們依循部落的年齡階層制度組織社群,在都市中延續年祭等儀式,緊密連結,形成都市聚落的故事;也刻畫身懷Pangcah文化底蘊的獵人,以及擅長樂舞的歌者,在城市中無用武之地,多數人轉而成為工業與建築業底層勞工,在城市邊緣開拓另一種部落生活的無奈與悲酸。趙慧琳的訪查與書寫,不僅記錄了這段歷史,也深刻呈顯了阿美族人從遷徙到扎根的心路歷程。
一九八○年代以後,臺灣社會開始進入轉捩期,政治改革與社會運動勃興,臺灣原住民族也出現了自覺運動,其中「還我土地運動」先後於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三年出現三次大遊行,為土地的流失及原住民族土地正義表達心聲。從社運訴求到其後的「原住民族正名與自治」議題到二○○五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都十分鮮明且壯闊。然而,都市原住民居住權的問題依然存在,加上他們在勞動市場的角色也轉而被東南亞移工取代。《Ina,太陽的城市》這部非典型的長篇歷史小說,在承載這段時代印記的同時,也以趙慧琳的新聞之眼、文學之筆,為臺灣原住民族群中人口數最多的阿美族寫出了族群記憶和歷史傷痕,令人為之動容。
今年適逢國藝會成立30周年,長篇小說專案已辦理22屆,補助83件計畫,是國藝會推動最為長久的專案。國藝會將持續以繼,鼓勵臺灣作家以長篇小說創造新歷史,廣開題材,開拓新領地。期望有更多寫作者投入這個書寫行列,讓臺灣的長篇小說開出更多花果。最後,也要謝謝斑馬線出版團隊為本書投注心力;謝謝長年贊助本專案的和碩聯合科技公司,為企業贊襄臺灣文學樹立典模。
推薦序
原視族語新聞-海岸阿美語主播 歐嗨.思娃娜(Ohay.Sewana)
月夜(作詞:黃貴潮 原曲:盧靜子/暗淡的月)
Hoy ya yo fariw ko asfalat
南風輕輕吹起
Fangcalay ko dadaya canglalan ko folad
今夜月滿十分 美哉呀
Mikipapotapotal sa ko tamedawmedaw
月光下左鄰右舍都出來活動了
A malaholol to fiyafiyaw awa ko kihad no Amis a tamedaw
大家見面彼此相問候 阿美族人天生知足樂觀
Mikipapotapotal sa ko tamedawmedaw
月光下左鄰右舍都出來活動了
A malaholol to fiyafiyaw awa ko kihad no Amis a tamedaw
大家見面彼此相問候 阿美族人天生知足樂觀
拜讀了趙慧琳的著作《Ina,太陽的城市》,腦海裡浮現了這一首部落一直傳唱的歌謠,是阿美族耳熟能詳的曲子,短短一段曲子就詮釋了阿美族樂觀豁達的民族性格。也讓我想起兒少時部落的生活,在夏天的季節3C設備還不普及的那個年代,到了晚餐的時間就會把餐桌搬到戶外,然後吆喝左鄰右舍一起malafi(晚餐),沒多久,每一家就端出一道或兩道菜來,熱熱鬧鬧,開開心心享用晚餐。晚餐都是那個季節時令的佳餚,或是ina從山上溪邊沿路採集的野菜,然後煮了kohaw(大鍋湯),也有隔壁的kaka(兄長)從海裡帶回來的foting(漁獲),每一道菜都非常鮮美可口。晚餐大人們彼此分享一天的工作,哥哥姊姊們天南地北的閒聊或歌唱,小孩們在月光下捉迷藏或追逐ponaponay(螢火蟲)。有些時候圍著(akong阿公)要聽他說 itiyaitiya ho(以前以前)的故事,空氣中充滿歡樂,這些都是我記憶裡部落最美的風景,是語言與文化(神話傳說)在小小的心靈萌芽。
部落是非常緊密的,幾乎生活裡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大家一起完成。如~種稻,從整地到收割,部落都是用malapaliw(換工)的模式互相幫忙。今天我到你家幫忙割稻一天,改天換你家派一人來我家幫忙割稻。若家裡沒有人可以耕作的獨居老人,部落的selal(年齡階級)會分工幫老人家打理,這個我們稱作pa'edap(青年代耕)。部落任何一家蓋屋舍,也是用這樣的模式進行,這是部落最特別的社會模式。部落是一個整體,如~部落要打掃及整理周邊環境,家家戶戶都得要pasorot(獻工)。若我家辦喜事,無須擔憂沒有人來幫忙,親友及鄰舍都會主動來支援,這個模式叫mitahic(幫工)。若家裡有往生者,部落有palamal(送溫暖/陪伴)的文化,這些都是在生活裡一點一滴的養成,已深植在每一個Pangcah(阿美族人)的血液裡,一個從母體傳下來的養分。
每年4月到6月是東海岸kakahong(飛魚)迴游的季節,部落早已在二期稻作收割後的空閒,開始整修dadangoyan / cifar(竹筏/木舟)就等待飛魚季的那一刻。部落沒有漁港,一切克難從簡,下午東海岸的太陽已斜斜掛在海岸山脈稜線上,dadangoyan / cifar(竹筏/木舟)準備下海,必須要大家一起合力推到浪頭,之後還得有人一直在岸上顧火,讓船上作業的族人有一個清楚的座標,猶如燈塔。直到月亮高掛,竹筏才陸續準備上岸,這時岸上族人已集結準備幫忙將竹筏拉上岸,這個動作我們稱它mihanget(牽罟),來幫忙的人都有漁獲可以帶回家。任何人上山狩獵有收獲也都如此,都會pafatis(分享),這是部落從過去一直延續到現在最溫暖的文化。
生活中的每一項參與就是學習,是成為真正Pangcah人的基礎養分。部落有太多密不可分的活動,工作mapolong(一起),吃飯mapolong(一起),做什麼都mapolong(一起),跳舞也mapolopolong(一起一起),是一個非常和諧的民族,就像我們在ilisin(祭典)時selal(年齡階級)各司其職,族人圍著圈手牽著手,齊聲吟唱對天地人的感動,和諧的舞步遵循先人的足跡。Ilisin(祭典)感恩的季節,不管任何一項祭典儀式,看見部落的rikec(緊密/凝聚/團結),聽見部落的活力,感受部落文化的傳承與永續。
文化已植入在每一個Pangcah(阿美族人)的細胞裡,從母體傳下來的晶片,一個必須用母語才能解密的文化精隨,因為理解了文化,母語才得以延續傳承。因此,當我們離開了部落,不管在任何一個地方落腳,來自母體的精神,會從這裡開始複製萌芽延伸,《Ina,太陽的城市》鉅細靡遺的詳述阿美族人的生活樣貌。
那一天見面,作者趙慧琳紅著眼說:「我來晚了,沒趕上讓夷將頭目(Cinemnemay吉能能麥都市部落前部落領袖 Mama Iciyang)親眼看到我已將書寫完了……」,沉默……。
趙慧琳親自送來她剛寫完的這一本厚厚的《Ina,太陽的城市》。聽她講述,當初到部落來來回回奔波做田調與拜訪受訪者,以及釐清的部落家譜氏圖,清楚的交代每一個受訪者的身世背景,及部落遷徙的過程和脈絡。我萬分感動與佩服,在沒有專人翻譯的狀態下,是什麼樣的動力激起她完成這樣一部鉅作。感謝她為阿美族人以生動細膩的手法,記錄了從過去到現在,離鄉背井到都會生活阿美族人的血淚史。深深感動她為《Ina,太陽的城市》此書所努力的一切,我要在這裡說聲:「慧琳謝謝妳!」。如果mama Iciyang 還在,他一定也會說:「Ahowiday! Tada calowayay a tamdaw kiso.(感激不盡 妳真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
推薦序
國民美術推動者 劉秀美(曾經在汐止花東新村陪伴都原兒童美術多年)
普世文明潮流轉現眼前,在上一世紀人們不敢言語的力量,已隨現代知識解放了,時代變遷中,過去舊蘇聯解體,老沙皇巨大俄國消失,地圖不是永遠不會更新展現新生存,世界的人類,強國在土地的欲望永不飽足,古殖民還有後殖民不停歇,在鐵蹄拖曳的善良族群殘骸耀威,現代終有普世的聲浪喚醒!各國原住民身份認同,臺灣也不例外,由思想面,可據理解決統獨問題,將臺灣命運系統改變,尋根到地理和土地的原始主權,蕭瓊瑞是臺灣第一個人寫臺灣美術史,從石器時代開始寫作,包刮古地圖也是美術,他開啓長久以來的思想革命,甚至比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目光和文化系統更遼闊而壯大,可惜文化界的美術圈無人接棒和喝采,就此精彩發現孤懸天際,幸而藝術家雜誌砸下重金,ㄧ口氣為蕭瓊瑞的臺灣美術史出四集,可惜的是蕭瓊瑞的第四集戰後篇,還是未能在田野發現傳媒和美術學術以外的地下力量,甚至連學院系統的陳來興的部分都未提及。
正義和堅強是臺灣本土目前惟一的路,只要想到外省人鄭南榕,和一些犧牲生命為救社會的臺灣人ㄧ樣,能夠堅強到如神明一樣,抗拒當年的思想暴政 ,讓臺灣從此有了言論自由,以外省人身份他並且充分了解臺灣的苦難和危機,願意用自己的生命換取臺灣旅程的下ㄧ步,我們從他所獲的教育,足以得到勇氣和毅力再走下去,如果思考鄭南榕,就能理解,面對所生存的土地 不要把自己當做過客,而是感動和疼惜臺灣成長的一切,和臺灣同甘共苦,才能立足世界,在臺灣的人永遠不變賣生我們養育我們的母親。
和慧琳的奇遇……
1地球有一半是漆黑的,在幽暗中有英雄的哭泣聲,他們被隔空高懸數千年,無光中細細保留語言到今天,
2自都市原住民青年湯英伸在城市求職遇害反抗後被判死刑,之後的社會幾乎很少有描寫都市原住民的書,在衆多文學表達中 這份著作需擁有特別的平等和文化選擇,我和慧琳認識於汐止山區未開墾的野地,花東新村,當時是民國85年,她以聯合報記者身份進入,那時的族人站在山頭,將國家法院寄來的傳票,捏成ㄧ團丟到山下,因美術課進行,ㄧ家男主人被叫了出去,當場打兩個耳光,被痛罵如何能公開這個地方給外人?這裡原來是高鐵修護預定地,屬於國家用地 阿美族人偷渡進來以他們精湛的技術用板模建立了村子,因為沒辦户口,孩子們到十歲還沒入小學。
3一個能用人道處理原住民的國家,才是真正的上軌道國家,六О年代的萬華華西街小巷,密密麻麻的私娼寮緊臨而居,原住民孩子,透過人口販子,和原鄉校長主任聯手,將原鄉孩子賣到台北,這些無能又貧困的人家,由父母們簽押收錢,北上的孩子被二賣三賣很多,等她們回鄉,已是老婦,當時華西街的暗巷點著粉紅色燈管,穿短裙的小女孩成排站立店前,她們的腿上全是自鄉村北上來的紅豆冰,點點蚊蟲咬傷的疤痕,夜深的時候,上鐵絲網的門窗,防止孩子偷跑,燙髮師入門為她們在室內燙髮,藥房接著進門打荷爾蒙針促進提早發育,原住民的都市經歷,從戰後以來從來無法致富,只是在城市淪落,一九九六年汐止花東新村的部落,是他們的遠夢,也在建立部落六年後消失於火災。
4雛妓~這個人類性市場最殘酷的買賣,落在了臺灣古老民族原住民孩子身上,悲憫和分享的感動,是一個社會是否能邁向希望和理想的精神國度,但臺灣在過去培養了學歷和金錢的社會,對於這些不幸,自然不會有良心的不安,講究高學歷的國家,目中無人的優越感,每個城鄉由最高學府的人士,掌握資源和舞台,無法做出公平分享的平等尊重,也無法教育下一代守信,尊重和誠懇的待人方式,當萬華的歷史揭發,它還有許多的慈悲和道德,挺住可憐的人,它來自平凡的普羅階級,而不是這些高級無情不懂人際和禮貌的高級知識份子。
導讀
《Ina,太陽的城市》是國人首部完成的都市原住民大河大海史詩,也是同為母系文化的平埔女性作者,向姐妹族裔的阿美族母親們致敬的跨族群性別寫作文本。
臺灣文學的歴史書寫,不乏多族群文化的原鄉溯源。然而都市原住民作為臺灣城鄉移民的一支,是城市多元文化不可忽視的貢獻者,更是過去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和居住權抗爭的時代舞台主角,卻一直欠缺族人勞動史詩的大型公共書寫。
阿美族人從原鄉遷徙到都市,已然超過半個世紀,形成了三到四個世代傳承的邦查都市部落。大規模北漂的勞動長征,並未剪斷族人和原鄉之間的文化臍帶。都市移工潮中的邦查集體離散,翻轉為文化種籽的長程播散,而非文化失根,也彰顯出族群的社會調適韌性。文化抵抗更成為都市部落扎根的隱形力量。這是《Ina,太陽的城市》 作者向邦查學習的寶貴資產。
都市原住民的移工潮並未結束。都市部落也是不斷再生的原鄉。《Ina,太陽的城市》作者趙慧琳集報導、田野民族誌、歴史小說,信件和論述等形式於一身的歴史書寫,也是當代進行式。臺灣文學的歴史書寫,永遠是有族群觀點和性別角度的書寫。《Ina,太陽的城市》是離散平埔女性作者寫給離散都原的未完成家書。
作者序
趙慧琳
《Ina,太陽的城市》的出版,值全球暖化加劇,地殼升溫導致臺灣島地震頻仍的氣候緊急年代。這部作品也約略是在我上一部作品《大肚城歸來》問市的十年後週期。我都要忍不住自嘲,這是在多族群地震重災後,不再適宜現地重建的斷層帶文學。尤其Ohay.Sewana 歐嗨.思娃娜為這本書寫序的邦查拼音母語優勢,更強化了我身為作者的自覺意識:即便費力探索一代二代都原的遷徙腳蹤,這部作品比較是平埔人觀點的漢文書寫,談不上邦查主體的原住民文學作品吧。
平埔寫作是在族群斷層帶上挖掘土礫堆中殘留記憶和歷史密碼,是永遠未完成的救援任務。拼湊不回來的。徒勞。當我只能理解都市原住民朋友的中文口說,形同踏上另一處文化斷層帶,讓過度輕率跳入邦查城鄉移民結界的我,幾度寫作胎位不正,瀕臨創作難產,才終於自救他救,重新有了呼吸。如果挪用漢語是片斷肢解的分屍,無力轉譯邦查的優美古語,那麼我的書寫就是慣於誇大其辭,又經常在轉角迷路的一群無家遊民。我說的是文字。
感謝都市/原鄉邦查慷慨支持我將鋼筋混凝土的書寫中文,為愛朗讀,讓部落母語讀劇會成為二創回歸口述傳統,解構重寫太陽的城市,給予我從中文泥沼中狼狽拔出來的解放時刻和救贖中繼站。新書發表是解構的喘息空間,是改寫再改寫的新實驗場域。請阿公、阿嬤、伊娜、法吉和法義們接力共筆。也請讀者們不要將印刷紙本的這部作品誤讀為人物精準對號入座的都市原住民歷史。虛構的敘事讓它離地展翅為空中的大冠鷲,越飛越遠的紀實之翼。
《Ina,太陽的城市》可能也不是文學;更像是報導,論述,民族誌,書信,以及非典型歷史小說的阿美族大鍋菜,盼讀者能夠在都市底層移工的早年苦澀記憶中品嚐到清甜的後勁。
《Ina,太陽的城市》沒有聲名顯赫的歷史人物,沒有族群領袖當主角的邦查時代英雄。
我的姪兒曾經在幼稚園階段的繪畫安親班中,畫出體貌逸出了白色圖畫紙的巨大父母。我一直記得,才藝班老師如何認真指正,無須將特寫人物描繪成天下無敵。可是我的姪兒當下滿臉驕傲,揚聲反駁。意思是在他眼中就是巨人。這也是我寫作原鄉/都市邦查的視角,越是都會漂泊中未曾留下簽名的勞動者,越是書中浩瀚篇幅的巨人,即使談不上豐功偉業的記事。
他/她們曾經是血淚受害者嗎?是,也不是。本書推薦序作者歐嗨有答案:古文化遺留已透過族群晶片的內置,在移動邦查的每日都市生活中,成為護身符。上善若水,不是大河就是大海;總是一起(mapolong);懂得換工智慧(malapaliw)的阿美族群文化,是都市原住民超過五十年集體抵抗歷史的致勝武功祕笈。包括母權至上ina在內的文化抵抗,是都市族群政治的終極腳本。這也是作者不肯妥協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