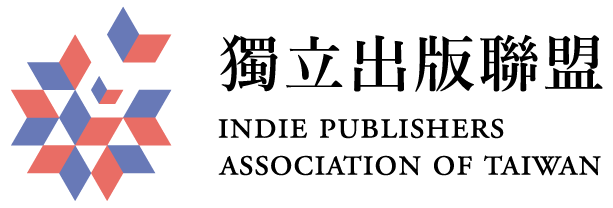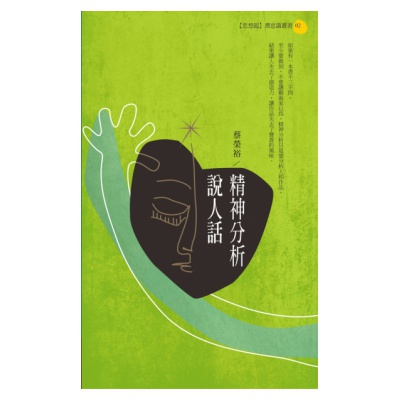
精神分析說人話
Publisher:
Publishing Date:
ISBN:
Format :
Category:
Price:
【思想起】潜意識叢書 02
內容簡介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經驗談》,這些都是中文世界裡很原創的文字,是從長年的臨床經驗裡萃取出來的精華,雖然不是提供快速的人生命題的答案,相信愈咀嚼會愈有滋味,那是文字和心理經驗結合對話的味道,有故事片段,但更著重心理想像的自由飄浮。
精神分析和藝術可以相互滋養,這不是理論而已,是本書想要實踐的事件。本書也有詩、小說和隨筆,它們之間有什麼可以連結的節點?那就是它們都說著人的故事,從不同的類型說著人的故事,並在故事裡想像人的侷限。畢竟不是只為了沈浸在故事裡,而是在侷限裡開展無限想像的可能性。 最後附錄一篇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技術主題《什麼是分析的態度?》。這是一篇長文專論,作者刻意不以學術論文的規格發表,期待是讓一般人可以刺激思考的文字,不論是否為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療者,都可以從閱讀裡擁有自己的發現。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蔡榮裕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醫師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資深督導
無境文化 【思想起 】潛意識叢書 總策劃
《都是潛意識搞的鬼》作者(無境文化 2016)
蔡榮裕醫師,學生時代參與高醫大學《阿米巴詩社》,之後在台北市立療養院(目前的松德院區)開始精神科的工作,期間與同儕創立《採菊東籬下》和《思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小組》為名的團體及刊物,陸續發表大量文字作品,大多圍繞著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間或有一些文藝創作。他的文字風格特異,下筆又如有神,其篇幅常常是同儕裡占最大比例,是最勤於寫作的一位。1998年赴英,至Tavistock Clinic專攻精神分析,兩年後學成歸國,帶動一批年輕精神科醫師前仆後繼、負笈英倫學習精神分析的熱潮。
蔡醫師從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的專業領域,到詩、散文、小說及戲劇的文學創作,乃至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的重大議題,永遠有源源不絕的思想靈感。其中,與林玉華教授前後耗費十年合譯完成的精神分析皇皇巨著——《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1941-1945》(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1945),更是經典的里程碑。
2004年蔡醫師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有識之士,共同創立「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同時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連上線,經過十來年的辛勤奮鬥,終於在2015年 7 月正式以Taiwan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名稱成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機構,此後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地方以自己的語言進行「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認可的分析師訓練。
序
序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經驗談>
什麼,生命的某個階段被卡住了?
你重複提到「一切都被卡住了」,好像生命的困頓都是因為生命的某個階段被卡住了。
雖然什麼叫做生命被卡住?是令我困惑的字眼,聽起來很具體的字眼,到底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如此肯定的態度和口氣,好像你要告訴我,你早就有了自己的定義了,然後你在自己定義的語詞裡讓自己被卡住?這種卡住也導致困頓的感受,然後你就有了目前的問題?
我相信這些描述不是很容易了解,不過卻是你來求助的緣由,這些語詞的使用理應有你個人獨特的用法,也可能包含了當代社會裡的一般用法。
例如,你提及在大學時期和家人發生了衝突,家人只要你好好專心讀書,不要多交朋友,你從心底覺得不同意但你都配合了。後來卻愈來愈覺得不可行,有股心聲催促你一定要多認識一些人,當你後來開始這麼做,你卻覺得一切都太晚了,你說這也是你在家中的感覺。
你覺得父母給你的不是讓你更有天空可以想像,你覺得父母只是要你依照他們的意思去做,後來你發現照他們的做法根本不可行,你也覺得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但你覺得太晚了,「一切都被卡住了」,你覺得沒有出路了。
我很好奇這種一切被卡住了,這是什麼意思?是在什麼情況下和什麼心理世界裡,會浮現所謂「一切」這個感受?我可以感受到你是很真切地覺得,當你的生活變成那樣子時,這種一切都太晚了的感覺就跑出來了。
不過,我還是好奇我的不解,到底是什麼情況下會浮現這種「一切」的說詞?這種一切的說詞真正意味著什麼呢?實質上它是包括了什麼,才會讓人覺得一切以及一切都太晚了?
你說很恐慌覺得被卡住的情況,讓你的未來註定是平淡的。你不喜歡這樣子,你想要有一條不同的方向和可能性,但要著手實踐時,你發現周遭的人都是站在你的對立面,你也就再次被卡住了。這種說法是有人在對立面時就會有卡住的感覺?
你每次說出被卡住了,難道都是一樣的嗎?我假設是有所不同,雖然使用相同字眼,也呈現相同感覺被困住了,如果細看和想像,我覺得你是在不同的感覺底下,只是我還無法找到不同語言來表達這些不同。
你用相同字眼來說明,如果我也認定是相同的意義,那就是你沒有改變,但果真如此嗎?是否也有改變了,至少對我的想像有些微改變了吧,因為一起合作的時間漸漸久了後,而有慢慢的變化吧。
如果使用純粹卡住的說法,好像這麼說時就意味著,自有解決的方法在這個名詞裡,這個方法就是「讓自己不要被卡住」,所以就動詞來說就是如此簡明了,但是這種一看就有解決之道的說詞,何以讓你覺得如此困難呢?好像只要做出反面的舉動就可以了嗎?
我再進一步想,你是有提及一個主詞,那就是指「生命」被卡住了,所以真正的難題是這個主詞「生命」,或者已變成是受詞了,因為生命被卡住了意味著,有什麼東西卡住了生命,在後者的說法生命是受詞,被某個主詞的東西卡住了。
說法上是生命被卡住了,不是有東西卡住了性命,是否意味著仍得把生命這個說詞擺在主詞的位置,就算它落難了,不能將生命這詞放在受詞的位置,這又意味著什麼呢?這些只是語詞之辯嗎?或者另有其它的深意呢?這些名詞的主受詞的運用,展演出了內在心理世界的什麼景象,或深度心理學的某種態度呢?
我使用以下的比喻,做為了解這件事的這些想法,雖然使用相同的詞句,但就好像一開始時只談神木,也有談到小樹,後來有了小花,再後來有了苔蘚植物,也有了小蝴蝶等等。
在這個過程裡,你的視野已經不同了,但因某些重要問題仍存在,就以為好像完全無改變,但是當一個人從只看神木到看大樹到小樹到苔蘚的視野,你有可能沒有改變嗎?只是這似乎很難用說服方式讓你看見這些變化。
我舉另一個例子來說明,例如,人生終得一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語詞,我們能說個案談了很多後,仍覺得人終得一死,但是一些潛在態度有所不同了?雖然結論仍得一死,但我能說你沒有改變嗎?
有人說這是最後的「見山是山」,只是對於這種容易做出來的結論,我總是抱持著謹慎的態度,畢竟如果假設生命的複雜,何以會這麼容易就結論出簡易的內容?
倒不是結論的說詞本身的問題,而是要做到這種簡易的結論,要花多少代價呢?或者相信了這種結論後,要付出什麼代價呢?
尤其愈容易被推衍出來的這種結論,對我來說,其實是愈困惑而不是明朗化,但是我的說詞好像跟大部分人的經驗是相反的,因為也許會覺得好不容易推出了這種結論可以做為安身了,我的疑問卻又打亂他人原本努力所做出的結論。
前述的反應也是有道理,也要被理會,這也是我在目前書寫裡想要說明的,只是如果回到診療室裡就不是那麼單純,並不是我只要在你面前,將我的疑惑都攤開來,讓你一起想,然後以為這樣子就是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了?不過,這不是我的目的,目前書寫的這些疑問是事後坐下來好好想時才浮現的。
至於在診療室裡的情況,就不能以為只要攤開問題就是心理治療,這可能變成只是在進行殘忍的疑問,像是某種暴力,也就是說治療過程是比目前的論述還更要複雜。必須有一個過程並找出各式語言,來形容這些零星或混亂的經驗,這些過程的描述都構成自己的一部分,也是後來覺得自己是什麼人?這些陳述也都只是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部分......但是很小部分的了解,如何和你提出的「一切都被卡住了」的「一切」抗衡呢?
<小說>
我朋友許文賓的十五歲
「南台灣的陽光一直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句話絕對是適合做結論的好句子,也是描述南台灣陽光的最好說法。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前中期吧,南台灣的舊庄這個小村落,大家都還互相認識,大部分土地還是稻田。
但後來改變了。
村人們大多鼓勵小孩將來要離開家鄉,另謀發展才有前途的小村落,它後來的確改變了很多。
現在,如果你要我找出印象中的舊庄村,我必須坦誠地說:「一切都變了。」我很難給自己一個理由,可以完全清楚何以我需要做這些回憶?或者當我說回憶時,到底指的是什麼呢?只因為這些事曾在以前發生,或者它們的發生,讓我成為目前的模樣?目前我只想說,我就是有一種需要回憶的衝動,但不是想在以前的故事裡,找到目前某些情況的成因;只想嘗試在這些回憶裡,描述某種令我難解的人情世故。
尤其是夏天的陽光,將風也吹昏了頭,變得有些慵懶地掛在枝頭,連葉子也叫不動,如老丈人說的:「夏天的風比較笨,找不到窗戶吹進來。」
那是高中聯考後的第三天吧。
賓仔突然跑來找我,我也嚇了一跳,原以為小學畢業後大家就難再碰面了。他住在仁美村,那是離舊庄有一小段路的村落,不知何故舊庄村的人以前很少提到要去仁美村玩,而較常往中庄村、翁園村方向跑。因此仁美的小村落就被我們村裡的小孩忽略了。
我住的舊庄有省公路從村落邊緣切過,好像是一個有流動的村落,往南(往下)去屏東與枋寮,往北(往上)去鳳山與高雄。仁美是遠離省公路的一個村落,我甚至到了開始當精神科醫師的第二年,才想起:「是否往仁美方向看看?」我已經無法知道那時候我看見的「仁美」,是否就是賓仔當年住的「仁美」?雖然可以想像的是,由於它沒有瀕臨公路,因此是相當慢吞吞的發展,像牛車慢慢走過寂靜的角落。
「我剛剛又看到了那隻白馬,牠的翅膀垂下來,低頭在遠遠的那片竹林裡喝水。那裡有泉水從山壁裡湧出來。」賓仔開口說他的發現。
也許我會慢慢想起來,賓仔談這隻白馬的事,是從什麼開始的?這天我騎著腳踏車要去找二叔,在中途偶然碰到賓仔,他就在小溪旁的那棵土檨仔樹下。他沒有看見我,好像在想著什麼事,是我停下來跟他打招呼。我們就這樣談了起來。
在那個沒有冷氣機的年代,我們都熟悉如何避暑,那天的確是讓我相當難耐的夏天,只有幾片不太成形的雲,像很沒有誠意的幾位小流氓,在藍色天空裡站著三七步,也好像水彩畫家在工作一天後,收拾畫筆時不經心地揮了幾筆白雲。
好像再怎麼努力,也撐不出有意義的一天。中午時候,農人們也都躲回家午休了。
那隻老鷹不知何時出現在天空。老鷹在天空裡上上下下飛揚,好像整個天空都是它的。
「我們卻還為了聯考有幾分而哀傷著,像受傷麻雀的恐懼,未來就要在我們面前,無情地關起門了。」我想著。
只見老鷹偶爾才動一下翅膀,就能上下自如。課本說老鷹善於駕馭氣流,我們以台語則說:「老鷹是『臘葉』,親像十二月冬天的葉子,在半空中,飄來飄去。」但是老鷹很難讓你找到它落下的地方,落下的臘葉則是可以撿拾起來,夾在書頁裡,要保存著某種難以說清楚的心情。
「唯一的方式就是將落葉撿起來,夾在書頁中間,等待來年的某一天,無意中再遭遇時,看看是否能夠說清楚那是什麼心情?」我想著:「也許我們就像小雞吧,看見老鷹時,趕緊躲入草叢中。」
我原以為賓仔要談高中聯考的事,因為我也一直擔心著成績,雖然考後當天就一題一題對過答案,應該考得很不錯,但離成績公佈還有一個月以上,變得不知如何過這種空白的日子。如果說是無聊的日子,似乎不止如此,但說真的很難說清楚那是什樣的心情?
我很高興再遇見賓仔。但我直覺不要談考試成績之類的事。這個話題也從來不是我與他之間的話題。
「我最好站遠一點,不要打擾到牠,以免牠又飛走了。牠的翅膀好漂亮,常常想去摸摸看,我知道根本不可能。」賓仔說。
中午時刻,悶熱的天氣一直纏繞著這村落,我對於賓仔談這隻白馬的事,我一點也不會覺得不耐煩,也許是我從來不會笑他胡亂想,他才會跟我談那隻有翅膀的白馬。
「我原想跑去找你,告訴你白馬的事,本想先來告訴你,然後一起去看,但我知道等我們去時,他早就喝完水離開了。」賓仔說。
我覺得他好像要說些其它的事,但我不是很確定,也就沒有多問了,只是靜靜地聽他說「他的白馬」。
小溪裡的水流聲,充當沈默時的背景。
那天的白雲後來變得慵懶,一副膽怯鬼頭鬼腦的模樣,卻一直停留在那裡好像被關在門外。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額頭,汗水從額頭被擠出來的樣子,賓仔也順手以右手肘擦拭額頭的汗水。
一群麻雀突然咶噪地從另一棵龍眼樹,飛到我們頭頂的這棵土檨仔樹。等他們都飛到後,卻又突然靜寂了下來。
如果使用超現實詩的寫法,也許可以說:「這些麻雀也飛過來了,他們想要靜靜地聆聽,那隻白馬,如何優雅展翅,飛到,我們不知道名稱的地方。」但是我想當詩人,已是高中以後的事了。
記得賓仔說過:「白馬一定不是住在仁美村,我己經花了很多年去尋找,幾乎找遍了仁美村的每寸土地,根本找不到。」
我想,我從來不曾真正了解何以賓仔要講這些話,或者何以要花那麼多力氣去找白馬的住處?好像無事找事做,但是高中聯考剛過,怎麼可能以前會沒事呢?
就像我也不了解,何以我對這個白馬的故事,不曾覺得那只是胡謅出來的故事。我的確不曾如賓仔那般,想要去找白馬的住處,甚至也不曾去白馬常出現喝水的竹林。這一切好像仁美村是我們舊庄村的小孩常忽略的村落。
望著穿透芒果枝葉而落在小溪裡的陽光,我的心情卻莫名地哀傷起來,隨著流水帶來了令人哀傷的曲調。我很快地將那股哀傷,隱藏在溪水的聲音裡,我不想影響賓仔的心情,他今天看來是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