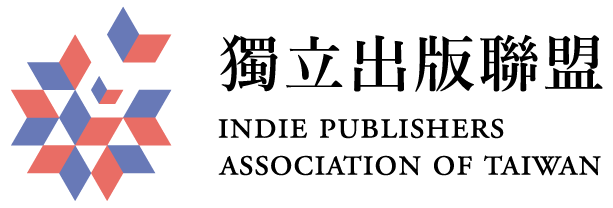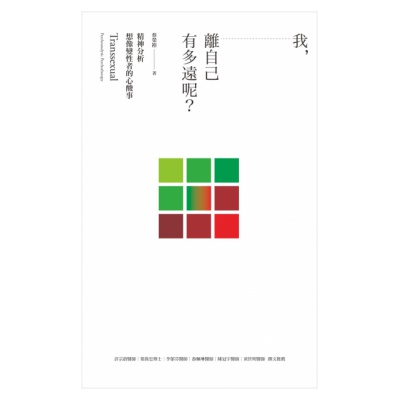
我,離自己有多遠呢?:精神分析想像變性者的心酸事
Publisher:
Publishing Date:
ISBN:
Format :
Category:
Price:
【思想起】潜意識叢書 06
內容簡介
「你說,你是雲,是逗留在人世間的雲,因為多了一根東西,而沈重得,無法飛上天。」
想要變性的個案,以努力賺錢、累積足夠手術費、割除命根子為心願;手術前夕卻因對未來感到擔心、不知自己喜歡男人或女人、不確定是否要當女人等等,種種矛盾和莫名的不安而來尋求分析治療。
多年後,分析治療師回憶這段兩年多的治療過程,化為詩意又苦澀的三十篇小小說。「如果三十章的文字,只是在重複地述說,我其實不了解你,我也不會覺得是誇張的說法。但我並不會因為我不了解你,就要推翻在這兩年多的過程裡,所可能產生的一些隱微,卻仍難以言喻的影響。因為我也很難相信,會毫無改變,因此也可以說,這三十章的文字,是試圖接近那一些些的影響。」
另有五篇雜文,是分析治療師以上述變性者為例,從精神分析的技術核心:「詮釋」之外,試圖思索還有哪些技藝值得開展?也道出了分析治療師的困惑和省思。「當分析治療師隨著經驗的累積,有了更大的信心,因而想要表達自己理念和技術,意味著把自身的經驗當作是一盞明燈,就算是分析治療師可以不這樣期待,卻常是個案投射給治療師的角色。由前述案例經驗的思索,是否目前光明的理念和技術,在未來可能是暗影的一部分?」
「從書名開始,我們就面對『我』跟『自己』的距離。『我』跟『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語言難道不是指涉一樣的東西,這兩個詞交替被使用嗎?但當分析師/分析治療師試著聆聽個案在治療室的語言,暗暗對照懷裡揣著的地圖,『我』不只是ego,『自己』也許指涉的不單是self,當個案說要『做自己』,暗指的是現在的我還沒能做自己,那甚麼樣子才是自己該有的樣子?是Winnicott說的true self,還是ego-ideal,或者我們有某一種模糊想像的ideal self,想像那個自己是除了現在的我之外的一切可能性? 」(游珮琳醫師/推薦序)
「我們總是想讓世界簡單一點,因為複雜的事很難理解。那麼,我們也可以讓自己簡單一點嗎?簡單,就是專心想一件事,把人生目標聚焦在某個點,某個可能性,全力以赴,讓一切以這個點為重心。個案老早下定決心動手術,努力工作,立志好好存錢,一切就是等待夢想實現那一天。一切都很清楚,是嗎?
『我要動手術,拿掉我不想要的東西。但我不知道該不該叫做變性?』(第一章)
這『不知道』,或許是因為『不想成為男人』並不自動等同於『想成為女人』。後者,是朝向某個目標;前者,則是遠離,是解開連繫。或許,有時我們以為,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達到某件事;但到頭來,也許其實我們一切的努力只是為了逃避什麼?」(黃世明醫師/ 推薦序)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蔡榮裕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資深督導
高雄醫學大學《阿米巴詩社》成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委員會副主委
序
推薦序
一千種聆聽的方式
游佩琳醫師
精神分析的聆聽有一千種方式,書寫有一千種方式,閱讀也有一千種方式。
先講一段拉維老先生的軼事。據說他有一位躺椅分析的個案,中年男性,好幾個月來,始終規則出席,但是不發一語。拉維老先生與被分析者一起沉默了幾個月。有一天,這位男士終於開口了:「謝謝你,Monsieur Lavie,我覺得好多了。」
跟蔡醫師相熟的人,也許會發現,他的書寫,簡直就像他的說話打成逐字稿一樣,翻來覆去到底說些甚麼?好像沒說甚麼,卻有臨床及理論浸淫二十多年的人才有的深度;好像是說清楚了,又留下無限想像空間。這本書讀完也有這樣的感受,非常口語的文字背後,卻是密度很高的理論思辯,觸及的是精神分析最基本的幾個概念:無意識、移情、詮釋、自戀、自我/自己(自體),乃至於臨床技術。你好像覺得自己懂了甚麼,碰觸了一些,但又驚覺抓在手上的鳥背後的那一片天空是不可能被一把攫取的!
此處我的閱讀,則是將這本書看成對悖論(paradox) 的思考。從書名開始,我們就面對「我」跟「自己」的距離。「我」跟「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語言難道不是指涉一樣的東西,這兩個詞交替被使用嗎?但當分析師/分析治療師試著聆聽個案在治療室的語言,暗暗對照懷裡揣著的地圖,「我」不只是ego,「自己」也許指涉的不單是self,當個案說要「做自己」,暗指的是現在的我還沒能做自己,那甚麼樣子才是自己該有的樣子?是Winnicott說的true self,還是ego-ideal,或者我們有某一種模糊想像的ideal self,想像那個自己是除了現在的我之外的一切可能性?我跟自己的距離,是切掉一根陰莖就可以達到嗎?而精神分析為什麼「想像」變性者的心酸?是因為他人的心酸一如無意識,我們只能夠逼近,透過種種表徵如語言、動作、夢,來試著貼近想像,但永遠無法說我們已經到達、已經瞭解嗎?有沒有開著Google map卻還是迷路的八卦?
書一開始「小小說」講的是治療室的場景,但那場景如此真實,我立刻困惑於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是男還是女?我們習慣的男作者蔡醫師,但描繪變性者的訴說對象,一名女性治療師,一個生來就沒有「命根子」的被閹割者。作為臨床工作者,我想像個案的訴說會如何受對象的生理性別影響(以及他怎麼想像聆聽者的生理性別如何影響他/她理解自己的角度) ;而作為一名生理女性讀者,我對「命根子」這個詞彙的感受是甚麼,應該跟男性讀者不同吧?我的想像是預設立場,還是它真是一堵連精神分析的方法都無法超越的高牆?明明我們都具有bisexuality,還是說解剖構造的不同遙指了佛洛伊德仍然時不時受困於生物決定論?所以我們只敢說「想像」,畢竟如書中一直強調的,當我們以為自己聽懂了,是不是就關上了窗,我們真的以為給了詮釋就點亮了燈,畫下句號?一如Thomas Ogden(1997) 說的,語言是精神分析中,被分析者與分析師用來溝通的工具,它必須在「講清楚」的同時還存在一個「沒被說出來」的曖昧性。換言之,當分析場景裡的言語都帶著確定,講的人跟聽的人都認為「就是這樣,對」的那一刻,思考已死,溝通已死。
不管是小小說的場景,或是本書後半部理論的反思及書寫,蔡醫師都大量運用比喻。佛洛伊德自己也不斷用比喻來闡述理論,或者我們該說,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理解,終究需要回歸到比喻的象徵意義。命根子是比喻,恐龍是比喻;拿走油燈或給予飢餓者菜單是比喻,空洞如家鄉或廢墟也是比喻。伊底帕斯情結說到底也是一種比喻! 既是比喻,我們所想表達的跟別人所理解的,是否就產生一個縫隙,而縫隙造成的後果,是斷裂,還是從這個縫隙中開出一朵甚麼樣的花?
回到Lavie老先生。那一年他來台灣,去1930巴黎餐廳吃飯。席間有人問,為什麼餐廳取名1930?那一年巴黎有甚麼特別值得紀念的事嗎?Lavie聳聳肩說:「不知道耶,那年我十歲!」
如果有一種智慧,能夠在手上握著精神分析的地圖,身上帶著滿滿的臨床經驗,但卻永遠保持赤子之心,大概就是這樣吧?蔡醫師致敬的對象,也是我們很多人心嚮往之的方向。這一系列的書寫也象徵蔡醫師在精神分析的山林中,以過來人的姿態幫我們綁絲帶做記號吧!身兼開路前鋒登山嚮導及火車頭的蔡老大又出新書囉!